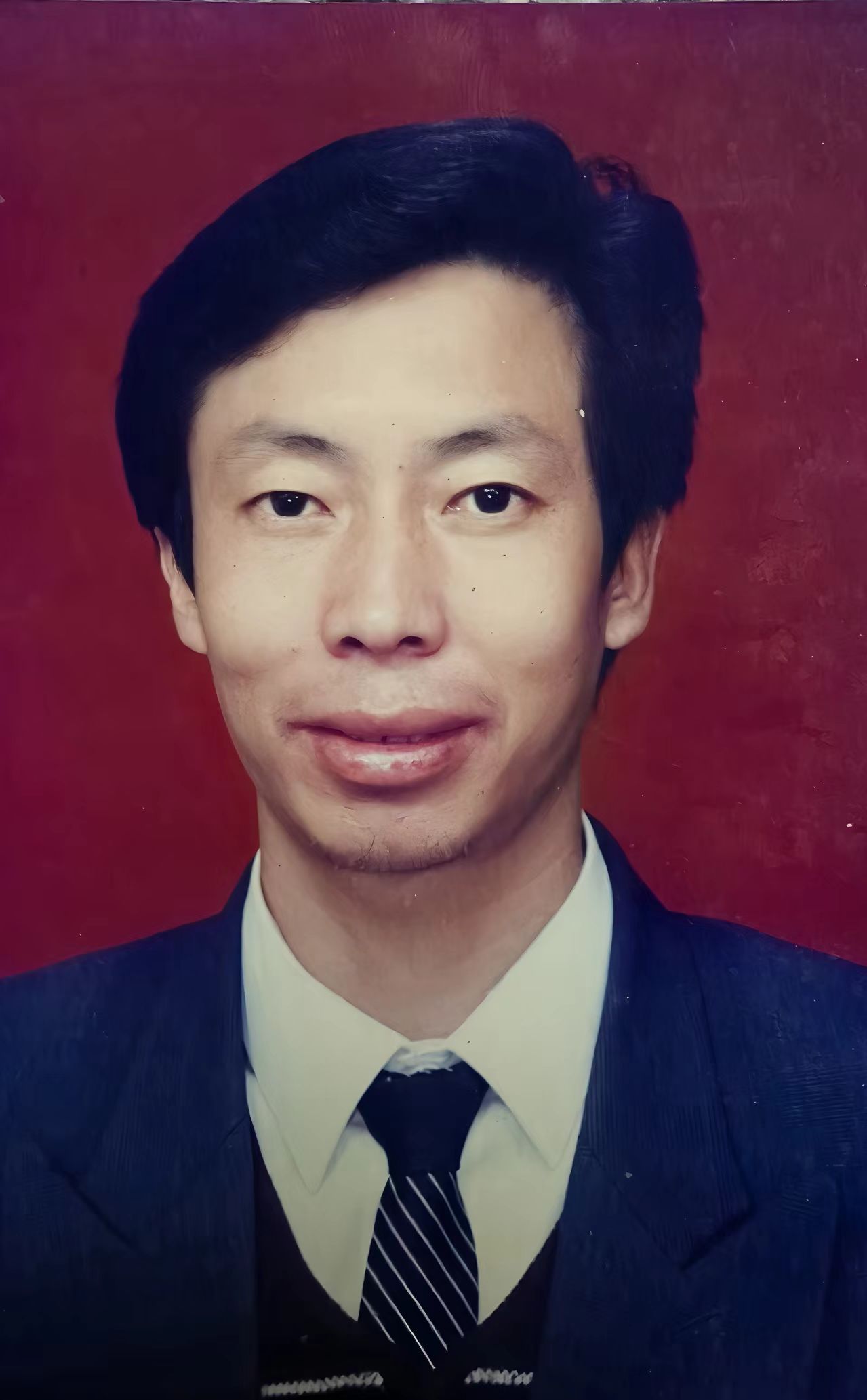三潭印月,水墨里的时光
三潭印月,水墨里的时光
杨斌旺
这一日,我与妻明春的西湖之约,便从这“断桥残雪”的清晨开始了。时值五月,自然无雪可寻,但那晨雾,却给了我们另一番馈赠。湖上的薄纱,软软地、厚厚地铺着,将远山近水都染成了一幅洇湿的淡墨。堤岸边的荷叶,已是亭亭,在微风里微微地抖动着。那雾气便缠在叶边,凝成一颗颗饱满的、晶莹的珠子,在叶心里滚着,闪着碎钻似的光。游客是早已有了的,三三两两,却并不喧哗。更有那许多打太极的,白衣飘飘,在堤上缓移慢推,人与景,便一同融在这无边的静气里了。
我挽着明春,踏上这白堤的起点。眼前的拱形石桥,静静卧着。我知道,眼前这桥是一九二一年重建的形貌了,桥畔那康熙御题的碑亭,也透着岁月的沉静。冬日雪后,那“断桥不断”的奇观,今日是无缘得见了。然而,在这晨雾里,它却另有一种风致。那弧形的桥洞,在氤氲的水汽中,显得愈发柔和,仿佛不是石头砌成,倒像是画家用淡墨在宣纸上轻轻一抹,晕染开的。我忽然想起那《白蛇传》里的故事来。许仙与白娘子,那一场惊心动魄的相遇,便是在这里么?眼前的雾,仿佛也成了那千年之前的雨,迷迷蒙蒙的,藏着一段欲说还休的深情。这桥,因了这传说,便不单是一座桥了;它成了一桩心事,一个印记,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来访者的心上,也压在悠悠的湖水之上。
离了断桥,我们登上一艘西湖的画舫。船慢慢地向湖心荡去,将岸上的喧嚣与人影,一点点地揉碎在橹声灯影里。外西湖的水面,开阔而平朗。途经阮公墩时,只见一座绿意葱茏的小岛,静静地浮在水上。我想起清代学者阮元疏浚西湖的旧事,这岛,便是那时堆筑而成,与湖心亭、小瀛洲鼎足而立,共称“湖中三岛”。这湖山,原是历代的文人墨客、贤臣良吏,一代代经营、一点点妆点出来的。我们今日看的,又何尝只是山水,分明是那层层叠叠、积攒了千年的人文厚度呢。
船抵小瀛洲,也便是三潭印月所在了。登岛,迎面便是一座九转回环的九曲桥,朱红的栏杆,在绿树碧水间,显得格外醒目。人说这是南宋皇家园林的遗法,为的是“移步换景”。我们缓缓走着,果真如此。身子稍稍一转,眼前的景致便全然不同了:方才还是一丛翠竹掩着亭角,转眼便是一池清水映着天光;才觉着路径已尽,忽地一折,又是一片开阔的湖面,将那苏堤的烟柳,遥遥地送了进来。这般设计,实在是巧妙得很,仿佛这园子是有生命的,懂得与人嬉戏,懂得在你不经意时,给你一份小小的惊喜。
行至“开网亭”,这是一座清代的六角小亭,名字取得极好,“网开一面”,透着佛家的慈悲与宽宥。那亭内的藻井,彩绘虽有些斑驳,却仍能辨出乾隆年间的样式,繁复而古雅。再往前,是闲放台的遗址,南宋理宗皇帝御书的“放生池”三字,刻在石上,历经风雨,字迹已有些模糊了。台前的水域里,果然有无数锦鲤,成群结队地游弋,红的、金的、白的,交织成一片流动的锦绣,在清浅的水波下,闪着粼粼的光。这“放生”的传统,竟已延续了千年,看着这些无忧的鱼儿,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安宁。
此行的主客,自然是那三座石塔了。我们走到“我心相印亭”前,这便是观赏三塔的最佳处。亭子的花窗是镂空的,设计得极为精妙,人立于窗前,目光穿过那雕花的孔洞,恰好能将远处水面上三座亭亭的石塔,一齐“框”了进来,仿佛一幅天然的画。塔并不高大,约莫二米有余,相传是宋时苏东坡疏浚西湖后所置,以为标志。塔身中空,球形的塔体上,环列着五个小圆孔,据说暗合着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之说。我凝视着那五个小小的孔洞,心中忽然浮起中秋夜的盛景来。那时节,人们在塔内点上灯烛,用薄纸将孔封住,那柔和的灯光便从五个孔中透出,映在水上。而天上的月,水中的月,塔灯的影,光与影交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共便成了三十三个月亮了。这是何等的巧思,又是何等的诗境!眼前的湖水,在我眼里,仿佛也浮起了那梦幻般的光点。
中午,我们在小瀛洲的茶室小憩。这临湖而建的明代风格建筑,窗外便是万顷碧波。我们点了两盏龙井,配着一碟清甜的西湖藕粉。茶艺师是个沉静的姑娘,为我们演示着宋代的点茶技艺,那一道道繁复而优雅的程序,仿佛将时光也拉得慢了下来。茶香袅袅中,望着窗外苏堤的倩影,一时竟有些恍惚,不知身在何年了。
下午的行程,便交给了雷峰塔。如今的塔是二零零二年重建的,铜制的塔身在日光下闪着金辉,里面竟还有电梯,可直上顶层。塔内的地宫,陈列着吴越国时的鎏金铜佛像,肃穆庄严;四壁的彩绘浮雕,则鲜活地演绎着白娘子的传奇。站在高高的观景台上,整个西湖尽收眼底,方才走过的小瀛洲,此刻也成了碧波中一枚青翠的印章。望着这塔,我忽然想起高中时读过的鲁迅先生的《论雷峰塔的倒掉》。那时年少,只觉着鲁迅是在抨击什么,却不解其深意。此刻身临其境,方才有些领悟。先生所憎恶的,或许并非这塔本身,而是那塔下所镇压的、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灵魂,是那千年礼教的沉重象征。塔虽已倒掉又新建,但那种无形的、束缚人的东西,是否也真的随之而去了呢?这思绪,竟比湖上的风,还要凉些。
傍晚时分,我们在暮色里登上了夜航的船,沿着杨公堤,穿行于金沙港、茅家埠那些更为幽静的水域。天光渐暗,两岸的灯火次第亮起,雷峰塔与苏堤,都披上了璀璨的光衣,倒映在墨色的水面上,随着波纹,碎成万千流动的金蛇。船舱里,有幽幽的古筝声响起,是那曲《平湖秋月》。在这乐声里,看那“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意境,白日里一切的喧嚣与思绪,都渐渐地沉淀了下去,只剩下一片空明澄澈的宁静。
归程的路上,我与明春都默默着。杭州之所以被人们誉为天堂,我想,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湖好水,满目佳景。更因这水这景里,沉淀了太多的人文故事。是白居易、苏东坡的诗,是白娘子、梁祝的传说,是康熙、乾隆的墨宝,也是鲁迅先生那犀利的笔锋。是这一切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积淀,让这里的每一滴水,都有了文化的重量;每一块石,都浸透了历史的芬芳。我们这一日的游历,便像是从这深厚的积淀里,小心翼翼地舀起了一瓢,虽只一瓢,也足够回味许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