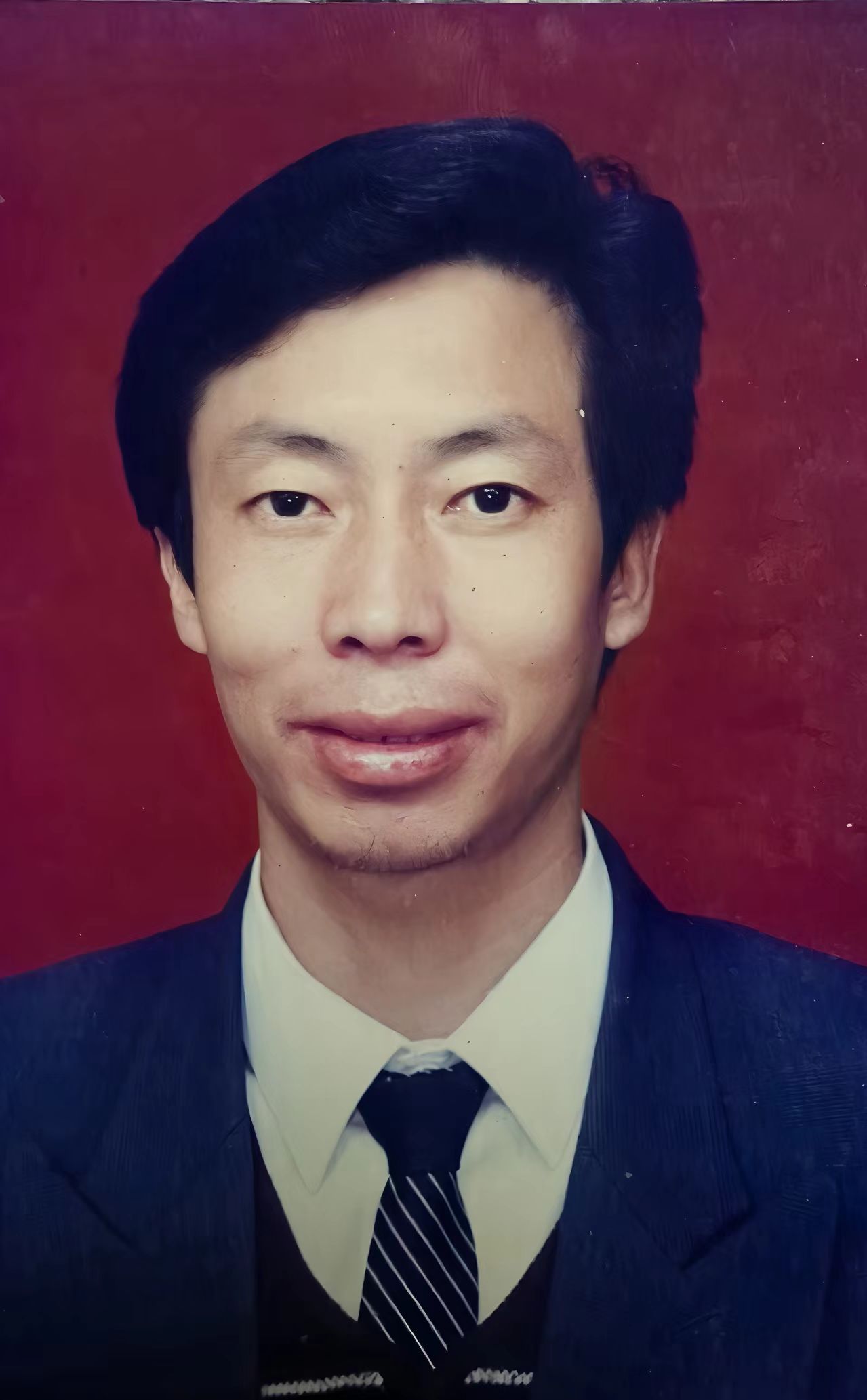西塘学养记
西塘学养记
杨斌旺
我们是从衢州出发的。两辆大巴,载着一百多颗暂别讲台与作业本的、略显倦怠而又期待的心,驶上了杭金衢高速。八月的晨光,是清亮的,带着水洗过的明净,慷慨地洒下来。车窗外,景致便如一幅绵长而舒缓的卷轴,徐徐地展开。那远山是淡淡的,近处的农家,屋顶上正升起袅袅的炊烟,是那种直直的、仿佛用尺子量着画的、青白色的烟。田野里,大块大块的金黄与青绿交织着,那是等待收割的稻谷与生机勃勃的千禾苗;风过处,便漾开一层层温柔的波浪。更有那成片的桔林,青青的果实累累地挂着,在枝叶间羞涩地躲闪。池塘里,荷叶是田田的,虽已过了最盛的花期,却仍有几支倔强的荷花,在碧绿的海洋里吐露着最后的嫣红。几只鸭子,悠闲地拨动着清波,偶尔“嘎”地一声,划破了这静谧的画图。还有那一列列整齐划一的蔬菜大棚,在日光下闪着银白的光,像是大地整齐的琴键。这一切,都让久困于城市喧嚣的我们,感到一种由眼入心的熨帖。
行行重行行,几个小时的颠簸,待到那股子属于古镇的、湿润而沉静的气息透过车窗漫进来时,西塘,便到了。
我们与西塘的初遇,是在那闻名遐迩的烟雨长廊。一千三百米的临河廊棚,蜿蜒如带,将古镇的市井烟火与一湾碧水温柔地隔开,又巧妙地连接起来。脚下的石板,被岁月磨得温润;头顶的木梁,黝黑中透出历史的质感。导游说,这廊棚起于明万历,而今我们触手所及的,多是清道光年间的遗存了。廊柱上,嵌着小小的石碑,刻着“船捐功德”字样,字迹已有些漫漶。我驻足细看,仿佛能听见数百年前,那满载货物的舟船在此停泊,商贾们慷慨解囊,为修缮这河埠、这廊棚,也为自己的生意与心安,积下一份功德。那时节,这河水该是如何的繁忙,这廊下又是如何的喧嚷。
离开长廊,我们转入石皮弄。这真是一条极窄的巷子,宽仅零点八米,两人相遇,须得侧身方能通过。两侧是高耸的马头墙,将天空挤成细细的一线,所谓“一线天”,便是如此了。导游让我们看脚下,那二百一十六块薄薄的石板下,竟暗藏着玄机。原来底下是立体的排水系统,每块石板边缘,都有精巧的榫卯凹槽,一旦落雨,雨水便能迅速导流,从不淤积。这明代的工匠,竟有如此智慧!在弄堂中段,我仰头望去,除了那一线天光,还瞥见墙上有嵌着的“界碑石”,那是昔日徽商与浙商划分势力范围的印记。这窄窄一弄,不仅通人,更通着历史的幽深与商贸的角力。
七绝
长廊迤逦接烟津,
石板青青迹已陈。
千载舟楫捐功德,
一湾碧水照商人。
登上卧龙桥时,已近午时。这是西塘最高的一座石拱桥,建于康熙年间。桥身那糯米灰浆的工艺,至今仍使得桥体坚固如初。用手抚摸那斑驳的桥栏,粗糙的质感直抵掌心,仿佛能触到三百年前的体温。桥东堍,立着一根不起眼的石柱,上面有深深的、无数道绳索勒出的痕迹。那是纤夫石。我凝神许久,耳边似乎响起了那沉重而有力的号子声,看见了那些赤着膊、弓着背的汉子,用尽全身的气力,将一船船的漕粮、货物,从历史的深处,一步步拉到现在。
午饭后,我们在环秀桥上怀古。这座单孔拱桥,竟暗合着二十四节气,每块栏板的浮雕,都对应着一个节气的农事场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古人的时间观与生命观,就这样被镌刻在坚硬的石头上,与天地轮回。桥洞内侧,有一片异样的灼痕,颜色深黑——那是太平天国时期火炮留下的战争印记。一瞬间,田园牧歌的想象被铁与火的现实刺破,这柔美的水乡,也曾经历过血与泪的洗礼。
而后去西园茶叙,在复建的园林中,于“听雨轩”里品一盏正宗的熏豆茶。茶盘里,青瓷碗、白瓷杯、紫砂壶,依次摆开,是为“三道茶”。青瓷碗里的熏豆茶,滋味清涩,恰似少年;白瓷杯中的菊花茶,色泽明澈,宛若中年之通透;紫砂壶泡的普洱,醇厚绵长,正是晚境的写照。这不只是茶,是江南文人将生命哲学化入日常风雅的智慧了。
圣堂的戏台上,正演着《五姑娘》的选段。那唱腔悠悠,据说还保留着宋代《鹧鸪天》词牌的韵律,是南戏的活化石。我仰头看那正殿的藻井,二十八星宿彩绘绚丽依旧,它们和这古老的唱腔一样,在时光的流转中,静默地守护着某种精神的源流。
暮色渐渐浓了,我们走在塔湾街上。明清的老建筑静静伫立,朱念慈扇庄遗址的门楣上,那“七曲八弯”的木雕纹样,据说是融合了北斗七星与八卦的避火符咒。街尾的老酒坊里,飘出阵阵酒曲的芬芳,那配方已传了十二代,空气里浮动的,仿佛是百年的微生物仍在欢快地歌唱。
七律
窄巷幽深岁月遐,
石皮底下隐玄机。
马头墙刻商帮界,
糯米浆凝匠心血。
栏板节符藏稼穑,
桥痕炮火忆征鼙。
一湾碧水涵今古,
皆作寻常百姓家。
夜里下榻后,我终究是按捺不住,又被那静夜的橹声勾了出去。包一艘传统的赤膊船,在墨色的水面上滑行。船夫用的是“鸳鸯橹”,展示着“左橹画圆,右橹走方”的绝技。船行至安境桥下,他让我们细听。果然,水流撞击桥墩,产生一种奇特的共鸣,淙淙铮铮,竟如钟磬一般清越。这哪里是自然的巧合,分明是古代匠人利用桥拱弧度造就的天然声学装置,他们将实用的桥,点化成了可以演奏音乐的乐器。
永寿桥畔的百年老店里,我们品尝着非遗的美食:荷叶灰腌制的陈氏酱蹄,古法酿造的顾公酒糟,保留明代模具的邹大鲜云片糕。邻桌一位老先生,用三根手指优雅地持着酒盏,慢慢啜饮。导游低声说,那是宋元时期文人酒礼的遗存。我忽然有些恍惚,在这灯火朦胧的水畔,时光的层次变得如此模糊而交融,呷一口酒,你品味的可能不只是粮食的精华,还有附丽于其上的、千百年的风雅与讲究。
归来数日,西塘的影像仍在脑中盘桓。我想,每日里如我们这般奔赴西塘的游客,该有多少。那门票的收入,那沿街店铺的营生,确乎是让这方水土的百姓,就业的路宽阔了,生活也富足了。而这一切的生机,追根溯源,不正是来自于我们对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旧物”——那廊,那桥,那弄,那戏,那茶,那糕——的悉心保护与珍视么?它们不是死的标本,而是活着的、仍在呼吸和诉说的历史。我们保护它们,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怀旧的幽情,更是因为我们今日与明日的富足与安宁,其根系,正深扎在这片文化的厚土之中。
沁园春·西塘归后作
吴根人家,越角遗韵,碧玉环萦。
看檐牙叠翠,舟裁素练;石桥拱月,露浥空庭。
界石铭商,橹声说古,苔迹深深岁月停。
斜阳里,数碑捐功德,谁记曾经?
繁华暗逐波声,料夜夜星河浸画棂。
叹三茶悟境,浮生况味;一腔田歌,宋代遗音。
酱瓮藏香,糕模印古,匠魂千载水云凭。
凝思处,这江南底色,是文明。
最近发布
- 杨梅赋 2025-11-03 17:45:41
- 游太真洞记 2025-10-13 10:33:06
- 山水有痕,人文如歌 2025-12-18 08:39:29
- 《琉璃易碎》 2025-11-28 16:45:10
- 《油痕上的暗影》 2025-11-20 10:21:10
- 南极之光,故纸乡愁——读耕妥兄《乌溪江,南极“两栖湿地村”》 2025-12-26 08:34:32
- 嵊泗行记 2025-12-30 11:38:02
- 垂直之路 2025-10-30 15:24:38
- 三潭印月,水墨里的时光 2025-10-25 15:44:48
- 游龙井,话治水 2025-11-06 08:5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