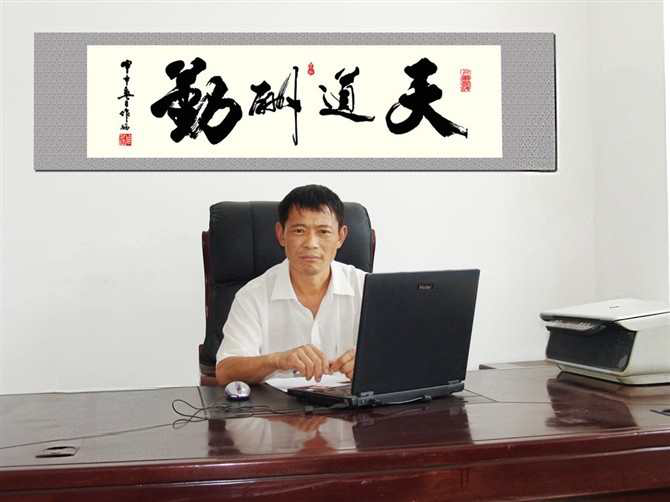解顺民:向光而行
解顺民:向光而行
落地青海西宁之后,我开始固执地认为,“凉都西宁”的美名必是风起的,不然何以如此凉爽!每天,风舒缓地吹着流云,让光为每一朵流云溢彩;风也吹着倏忽来去的面孔,留下短暂聚集的欢笑与荣光,送走长别时的不舍与惆怅。四天后,我又开始固执地笃定,历时四天的“第四届《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大奖赛颁奖大会”的荣光时刻,要比三年里沉淀的光阴更沉重。
与《中国散文网》结缘,催发我在写作上日日进步,直至走进辉煌的殿堂,时间追溯到2022年。记得那时是金黄的九月,从媒体获悉《中国散文网》正在举办第二届“三亚杯”全国文学大赛,对照自己刚完成的散文《丑妞》,于是,便抱着试试的心态投稿参赛,没料到获奖了。之后,散文《欲老未老》荣获2023年度第二届“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大赛奖、同年十月,散文《梦中的小清河》荣获第三届“三亚杯”全国文学大赛奖,诗歌《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一粒种子》荣获2024年“春光杯”当代生态文学大赛奖。今年,参赛作品散文《冬宰》又荣获了第四届“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大赛奖和“最美作家奖”。这一个个发烫的荣誉背后,是自己在每一个个生长季积蓄的力量所抛洒的笔墨,更是《中国散文网》无声的托付。
处在一个信息洪流奔涌不息、话语似乎从未如此丰饶、又从未如此廉价的时代,我的书写,是在喧嚣中为自己点燃一盏抵御精神迷雾的孤灯。它并非为了照亮他人,首先是为了确认自身的存在,向光而行,从记忆的河流中锚定并打捞那些即将被流逝的岁月冲散的点点滴滴。
在新疆,冬宰在游牧文化中从来不是简单的生产活动,而是一场凝固时间的祭祀。我写《冬宰》,更是想让读者见证一场来自新疆的史诗级的转场——它不是牧民传统意义上的季节迁徙,而是整个游牧文明向现代性疆域文明转变的悲壮跋涉。本质上是在记录这场没有地图的远征——记录铁蹄与器械、食盐与二维码、马鞍与区块链之间那些惊心动魄的碰撞和媾和。比如:老牧人,一手拿着祖传的银刀,一手拿着扫码枪,嘴里念叨着古老的祝福语发快递;比如:主播们穿着皮袄或棉大衣在风雪天用手机直播卖马肉马肠,但该产品加工的手法还是祖传的......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智慧的生存之道。正所谓传统和现代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像马肠里的肉和天然香料一样完美融合。当产品遍布大地的角落时,从来不是丢掉传统,而是在用新的方式延续传统,是面对时代变革最智慧的一种姿态。在写作过程中,我不断想起屠宰场另一种景象:检疫员用红外线扫描仪扫描马匹时,屏幕蓝光与哈萨克老人手中的银刀竟形成完美的互补色。这偶像的光学现象,恰似两种文明在冲突中达成的色谱和解。《冬宰》最终呈现的,正是这种在对抗中孕育的奇异和谐——就像马肉马肠在熏制过程中产生的美拉德反应,苦涩的摩擦终将酿成金黄的馈赠。当消费者咀嚼着鲜香的马肉时,他们不会知道每口鲜香里都藏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文明博弈。而作为生产者和作者的我,真正的使命就是让牙齿间的每一次咬合,都发出历史的回响。所以,你会在《冬宰》里读出冬天的结束不是死亡,而是为了孕育新的春天。
清凉的晚风深情地摩挲着离别的前夜,也会悄悄遛进窗棂,带来青海湖水的一丝咸涩,与我一起守候跳动的时针。台灯下,我让《轻轻的风深深的情》做音轨,串起三天里的流光拾贝,制成视频《夏韵——西宁律动》,发送到大会作家群里,使大家留住每一张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孔,留住大会上每一个感动时刻和辉煌的绽放。
当《夏韵——西宁律动》在动听的旋律中流出最后一帧、我乘坐的班机轰然起飞的霎那,我突然流泪了。这泪水不为离别,而是为曾经的相遇相知;为令人敬畏的邵总和老师们,正是他(她)们这多年呕心沥血、不懈努力地对文学人才的广泛挖掘和培养、我们才拥有才学展示和筑梦的平台;也为跳动的字节、奔涌不息的细节、喷薄而发的情节!!
忽想起临行前写给邵总的一首小诗,就用它作为此文表白的韵脚吧——
昨天,青海湖边/我双手捧起湖水/奋力抛向浩瀚的水面/那些被颁奖会烫平的平仄/突然在奖杯上长出羽毛/您日日的慈爱与微笑/滤镜了《净荷》/一枝压弯的荷花/仍固执地托付起原本的厚重/闪耀出圣经一般的光芒/于是,我把曾经的敬畏深埋心底/化作根茎去无声地延伸/汲取您赋予的每一份营养/直到《绿肥红瘦》/今天,那就把三天的感动装进行李箱/连同会场未尽的争鸣/抹去倒流的泪水/乘万米高云絮/继续挖掘伊犁河谷古朴的典藏
解顺民(笔名:唐布拉),中共党员,企业法人,文学爱好者,自由撰稿者,《中国散文网》高级作家,《中国作家网》会员,《半朵文化》专栏作家,作品散见于报刊及网络平台。部分散文及诗歌作品获奖并收录《全国文学精品选》和《最美中国诗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