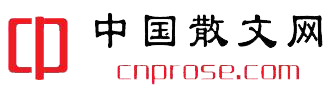曾记当年写春联
转眼间,过了农历腊月二十五,年越来越近,年味也越来越浓。趁回老家八尺沟出席侄儿许安的结婚喜宴的空隙,驱车前往原乡政府驻地北芙蓉,陪妻子去农贸市场转悠一番,只见大街上年画地摊好似一条长龙,由东往西热闹非凡:各种喜庆的对联、花边、日历、年画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望着这场景,思绪不由得回想起当年为村民们书写春联的岁月。
记得1993年4月,我从海河乡政府通过招聘考试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兴化电视台,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专职从事新闻宣传工作。
虽说进了城,但每年的春节都喜欢回来过。每到腊月二十五,我就会回到村里休假。名义上是休息,其实一刻也不清闲,相反地比以往更加忙碌。因为,我在乡亲们眼里被尊称为“大笔先生”。此时此刻,我家便门庭若市逐渐热潮起来。
一会儿,张家三婶、房家大伯、王家大爷、史家姨娘从村口的小卖部里买来红纸和墨汁,接踵而至,我家的小院很快被欢声笑语包围了。
“许先生,这是堂屋门的一副对联,这是厨房里的两个福字,还有窗户条上的两块横幅。”按照先来先到的规则,最先开张的是我家邻居史大叔,我根据他的要求,写下了“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大门对联,横批是“四季平安”,接着再写了两个端端正正的“福”字,窗户键的横幅则写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寓意春节期间一切逢凶化吉。
写好了一户,待墨汁风干后,接着再为下一家书写。村民房同根是村里的种粮大户,家里门多、农具多,每到写对联,他妻子三粉子总要买来三、四张红纸,他家一户的工作量相当于一般户的四倍,由于预先裁好,大门对联还好写,最琐碎的就是那些放稻谷的粮褶子,出行的挂桨机船、养猪养鸭养鸡的圈栏都要写上祝福语或者“福”字。对此,我心无旁骛,全身投入。稻褶子上写下“五谷丰登”,锅灶写了“人口太平”、猪圈鸭栏写上“六畜兴旺”;挂桨机船的两侧自撰“日行千里一帆风顺”“机器一响万事顺遂”,正对大门的墙上写下“开门见喜”四个大字。
就这样,我从腊月二十五一直写到大年三十中饭时刻,村里有一半人家的春联出自我手。腰酸背痛自不必说,一双手被红纸染得彤红彤红,但想到质朴憨厚的乡亲们“粗工伴细工”为我家掸尘、挑水、贴春联忙碌个不停的情形时,我忘却了疲惫。这种纯真的邻里关系,让人难以忘怀。
正当我收拾完备,准备吃饭时,三组五保奶奶宗兰英颤颤巍巍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佳荣,还写对联吗?我家还没有呢!”我见状,连忙说“写的,写的”。
心地善良的妻子拉着宗奶奶吃饭去;我赶紧从书房里拿出红纸,边裁纸、边磨墨,挥毫写下了“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感谢共产党”。
等宗奶奶吃完饭,我陪她回去帮助贴好春联,春联在太阳的照射下,把宗奶奶的脸膛映照得彤红彤红。此后,帮宗奶奶写春联成了我每年春节前雷打不动的分内事,一直到老人离世。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写春联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印刷精良、装帧新颖的春联。尽管春联五花八门,但总感觉缺少那种抒写的精气神,不知您有没有这种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