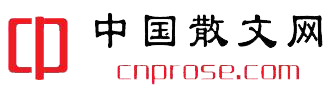《上海文学》2022年第9期|马修:镜中之鱼(节选)
冬
在我十一二岁,刚刚开始懂了一些人事的时候,我跟着祖父生活在那座古旧的城市里。那时小城的一切都还保留着更为遥远的历史时代风貌。我和祖父住在那个年代久远的机关大院里,办公楼和家属区交错而建,毫无章法,尤其是家属区,密集而散乱。而在大院的中间,却破天荒地保留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大花园,东西两角有一个小门出入。花园常年无人打理,除了鸡冠花、一串红,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花草肆意疯长,犹如丛林,昆虫无数,间错还有几棵高大茂盛的梧桐和苦柚子树。花园的四面有回廊,回廊另一侧是一间一间的办公室。白天,这里是办公区域,人来人往,到了夜里,花园变得漆黑一片,诡异骇人,却是孩子们探险捉迷藏的好地方,更是假日的乐园。
巴里亚就住在花园西门出口外面的联排平房中的一间办公室里,正对着我祖父家。那间办公室是一个套间,外面是他办公的地方,只有一张桌子、一个柜子,还有一个洗脸架,里间就是他住的地方。那间小小的卧室还有一扇门,常年关着,外面是一个长长的封死的过道,堆满了杂物。这间办公室基本上只属于他一个人,平日鲜有人出入。
巴里亚是在那年冬天来这里工作的,因为我记得在他来之前刚下过一场小雪。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母亲。她穿着一件不合时宜的深紫色旗袍,上身披着一件雪白的呢绒外套,头发是盘起来的,很有气质,也很端庄,长得也很漂亮,完全不像一个中年女人。来了没几天,她就消失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巴里亚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年纪,甚至更小。他是外地人,说电视里的话。关于他的身世背景,我一概不知,只听祖父私底下说他有间歇性精神病,嘱咐我不要与他亲近。
巴里亚很快被安排到我祖父负责的部门,一个安置即将退休人员的毫不起眼的清闲衙门。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看到巴里亚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很少出来走动或与人交流。起初没几个人知道他有病,也看不出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他为人和善礼貌,谦虚谨慎,言语很少。我听到很多大人在背后讨论他,说他是个美男子,只是太沉默了。的确,巴里亚长得很高,很瘦,成天穿一身黑色的不太合体的西装,越发显得他羸弱。他的头发是卷曲的,很浓密,眼睛很黑很亮,如果不是因为有病,怎么看,都是一个安静、帅气的年轻人。
直到下大雪那天,巴里亚不知为什么突然发病了。
那天我刚放学回家,正准备出去玩雪,只见他突然从办公室里跑出来,一边发出怪叫,一边脱了上衣,在雪地里打滚,见人就打。我吓得连忙躲回家。祖父闻声从花园里冲出来,又叫上几个胆大的干部将他堵住,捆了起来,送去了医院。
消失了一个多月后,巴里亚又回来了,还是正常上班。只是大家看他的眼光就变了。本来关于他的病情只是小范围知晓,算是一个秘密,平日里他也很正常。可他这一发病,弄得机关大院里谁都知道他有精神病了,都对他避而远之。孩子们也得到了警告。尤其是我,因为祖父家离他的办公室最近,只相隔一块不大的空地,几乎是正对门,所以得到的警告也最严厉。“任何时候都不要去招惹他”,这是祖父的原话。
巴里亚刚来那会儿,还有人给他介绍过对象。自从他犯病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和他接触了。为了保险起见,我的祖父也不再给他安排任何具体的工作。原本就寡言的他,变得更加沉默。我很多次上学放学,都看到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感觉他想出来,却又不敢出来,不知是害怕别人,还是害怕别人被他吓到,总之样子忧郁极了。
在我看来,巴里亚只是一个病人,可在别人口中,他被称为疯子。大家在私底下都这么叫他。事实上,我对他充满了好奇。或许是孩子对比自己大的年轻人,都有着难以捉摸的崇拜。我为什么会崇拜一个病人?我也不太清楚。也许是因为他看到我时,总是会对我笑。他笑起来很好看,完全不像一个精神病人,反倒让我感觉很舒服。
唯一让我不解的是,巴里亚在大冬天里也穿得很单薄,但是他似乎并不冷,我从未见他哆嗦过一下。
有时我去花园里玩,会经过巴里亚的办公室门口。他刚好在。我冲他笑了笑,他也对我笑,很灿烂,可眼神还是那么忧郁,仿佛有千言万语。
“你好呀,小朋友。”他说。
“你好呀,巴里亚。”我也用电视里的话回答。
这是他第一次和我说话。他的声音真好听,不像我们本地的方言,古怪难懂,也不好听。
不过我很快就跑去花园里了。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害羞。总之我跑开了。
快要过年的时候,有一天傍晚,祖父有事外出,我看到巴里亚办公室的门开着,里头亮着灯,好像还多了一个人。我便壮着胆子跑过去想找他玩。我站在他办公室门口往里探了探头,看见他正和一个中年女子在吃火锅。原来是他母亲来了。她还是和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的装扮,一身旗袍,外面套着一件呢绒大衣。
正是夜幕降临,天色暗淡,里面灯光昏暗。巴里亚看见我来,招手让我进去。他母亲热情地招呼我坐下一起吃,我客气地回绝了。可是她却执意拉我到她身旁。我抵不住火锅香气的诱惑,终于忍不住加入,一边吃着腊肠,一边悄悄地打量了一番眼前这个女人。她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浑身散发着不同于本地妇女的高贵矜持的气质。她脸上化了一点点淡妆,样子很好看,有一股说不出来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感觉。
“这是我领导的孙子。”巴里亚对他母亲说。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她声音很轻柔。
“我叫林达。”
“长得真可爱。”她摸了摸我的头。
她伸手过来的时候,我闻到了她衣服上的香味。真香啊。这几乎是我闻过最美妙的香味了。然后,他们母子安静地吃着火锅,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像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
“你最近还发病吗?”他母亲看着他问,眼睛里充满了爱意。
他摇了摇头。
“我明天就回去了……你一个人过年,要听话。”
他点了点头。
这是我唯一记得当时他们的对话。我就坐在他们身旁,像走进了电视里,看着他们表演。我想他母亲肯定在外地。她是干什么工作的?为什么要让巴里亚来我们这里工作?巴里亚的父亲呢?怎么从来没有来看过他?他父亲喜欢他吗?所有的一切,我完全不得而知。
春
过了年,他母亲又来过几次,还来我家拜访了我的祖父。她还托人给巴里亚安排了几次相亲。
巴里亚去了,结果却没有任何动静,始终还是一个人。
春天来了,他还是很安静地存在着。即使再悄无声息,在人们的眼里,巴里亚已经是一个异类,无从更改。可我却莫名地喜欢和他相处。或许那时我没什么朋友。孤独者和孤独者最是惺惺相惜吧。我的父母因为一场车祸不在了,我从小就跟着祖父生活。在大院里,我时常受到欺负。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宁可一个人玩。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院子里闲逛,巴里亚看到我,主动叫我过去,然后神秘兮兮地送我一只他抓住的麻雀。因为靠近花园,他的办公室时常会飞进一两只麻雀。他便立马关了窗户,直到捉住它为止。
“送给你玩。”他笑得很灿烂,“我是专门给你抓的。”
“谢谢。”
我当下感动极了。我想应该是前几日几个比我大一点的孩子抓了麻雀在我面前炫耀,他见到我难过的样子了吧。
“你真是个好人。”
“是吗?”他咧着嘴说,“你不怕我吗?”
“……嗯,你不犯病的时候,我就不怕。”
他的脸色一下就阴沉下来,样子很悲伤。
我立刻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连忙道歉。
巴里亚把麻雀的腿上绑好绳子,让我小心翼翼地捧着。他腾出手,摸了摸我的头,笑着说:“没关系,欢迎你随时来我这里玩。”
“一定。”这一次我回答得很干脆。
夜里,我把绑麻雀的绳子一头栓在桌脚,任由它在地上扑腾。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打算给它喂食,想不到只剩下一只脚爪子了。我难过极了,又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跑过去告诉了他。
“是被老鼠吃掉了。”他安慰我。没过几天,他又送了我一只。这让我对他又增添了几分好感,更少了一些戒备。
一个周末,我一个人玩得实在无聊,刚好碰到他推着自行车准备外出。他要去哪儿?我很好奇,他平常如果没有特别的事,基本上是不会走出大院大门的。我也一样。
“跟我出去玩吧?”他邀请我,看上去很期待。
“去哪里玩?街上吗?”
说实话,我很想去,可又在犹豫。祖父经常告诫我,机关大院这么大,已经够我玩的了,不许上街,尤其不许下河。更多时候,我总被祖父关在书房,写毛笔字、背书、做作业。但我经常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遥远的蓝天发呆,很久很久。
“放心吧,我不会犯病的。”他看出了我的顾虑。的确,这才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就去城外的加油站,”他又说,“我去见我的姑妈。”
“马上回来吗?”
“去去就回来。”
于是,我大胆地坐上了他的单车。他一路不时地跟我说话,感觉像换了一个人,变得十分开朗;不说话的时候,他便吹着口哨哼着歌,显得很开心。我很少坐单车,有些重心不稳。他让我搂着他。我照做了。他的腰可真细啊,好像我一使劲,就会断了似的。穿过闹市区,又经过一条长长的长满梧桐树的林荫小道,道路两边的房子越来越稀少,渐渐就出城了。城外是一片接一片的油菜花田。远处有小河。太阳很好,照得人很舒服。他一直没有停下来,我有点害怕了,不知道他会把我带到什么荒无人烟的地方去。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破旧肮脏的加油站,我松了一口气。到了地方,却没看见几个人。他带我找到了他的姑妈。他们一起坐下来闲聊,我就在一旁无聊地走来走去。过了没多久,她姑妈突然让我去看看加油站背后那个房子里有没有人,有的话,就叫他过来一下。我问是谁,她说,是巴里亚的姑父。我就去了。此时,加油站似乎就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我一个人战战兢兢地走过去,仿佛去往一个未知的充满恐惧的场所。我向来就胆小,害怕空房间,尤其是陌生的空房间,当然,还有夜晚空荡荡的集市。
我小心翼翼地找了一遍,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回来的时候,我冥思苦想打算用一个成语来形容没有人,前几天老师刚教的,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只好说,一个人都没有。他的姑妈就径自到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忙什么事去了。又坐了一会儿,巴里亚指着远处一条小河对我说:“我们上那边玩一会儿去吧?”
“好啊。”我觉得这里实在很无聊。
我们来到河边的一处草地上。和风吹拂,我们一起并排躺在草地上,晒着太阳。巴里亚嘴里叼着草根,闭着眼睛,什么也不说。这个时候,我一点也不感到害怕,甚至觉得他十分亲近。其实,那个时候,我很孤独,一直渴望拥有一个要好的玩伴、朋友。我还曾偷偷幻想过,如果巴里亚是我的兄长,我和他会如何在一起生活呢?我们的关系会变得更亲密吗?他如果是我们家的一分子,在家庭里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我总是这样,思维很容易就飞到别处。
“这里好玩吗?”他突然问我。
“当然好玩呀。”
“那我们回去吧。下次我再带你过来玩。”他起身,拍了拍屁股。
就在这时,巴里亚不知为什么,忽然开始全身颤抖,牙关紧闭,眼睛直直地望着田野上金色的油菜花田。
我瞬间意识到他应该是要发病了。这可怎么办才好?他会杀人吗?我应该跑开吗?我的确想跑,可是双脚像灌了铅,一步也挪动不了。我之前听祖父说过,到了春天,很多精神病人和狗看到油菜花就会发疯发狂。我来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这个呢?我感到十分恐惧,又紧张又担心地说:“巴里亚,你怎么了,你可千万不要发病呀,要坚持住。”
他明显听到我说话了,转头看着我。他的眼神是涣散的,死灰一片。他嘴巴嚅动着,想对我说什么,却始终没有说出来,身体继续颤抖。接着,他的双手突然开始拼命地搓揉自己的头发,身体却僵直着,定在原地,像在极力挣扎着什么,或者头脑中有什么东西要崩裂开来。他紧咬着嘴唇,表情十分痛苦。他是在控制自己吗?我想帮助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巴里亚突然停止了动作,却艰难地向我伸出手。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似乎是在向我求助。
我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
不,我的心被震撼了。我想,他是信任我的。我要帮助他!那一刻,我完全忘记了恐惧,勇敢地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像被冻僵了似的。他用力地握住我的手,全身还是在不停地颤抖。我的手被捏得生疼,却只得忍住。我望着他,他也一直盯着我,想说什么,仍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知道过了几分钟,或许更长的时间,巴里亚的颤抖终于停止了,眼神渐渐恢复了正常。他的身体也松弛下来,却已是满头大汗,脸色也变得异常苍白。他长长地吐了口气,对我露出一丝惨笑。
“你好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嗯。”
“你刚才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他大口喘息,良久,才又说,“林达,谢谢你。”
巴里亚瘫坐在草地上,像用尽了力气,后背上的羊毛衫都湿透了。他慢慢地调整呼吸。我当下很心疼他,为何他要经受这样痛苦的折磨,但也因此松了一口气。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控制住了自己,这让我觉得他其实很有力量。我想,他也不希望自己发病吧。但有一点,我可以坚信,在他握住我手的那几分钟里,他的确是在清醒地控制着自己。
回来的路上,他仍旧骑车载我,只是不像来时那样时而哼着歌或者跟我说说笑笑,而是一言不发。
到了机关大院大门。巴里亚就叫我下车,让我绕道穿过花园回家。他恢复正常了,脸色也变得红润。
“林达,记住,”他微笑着叮嘱我,“到家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跟我出去玩过哦。”
……
(本文刊载于《上海文学》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