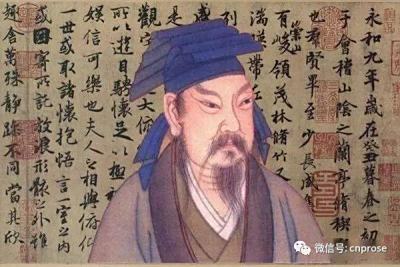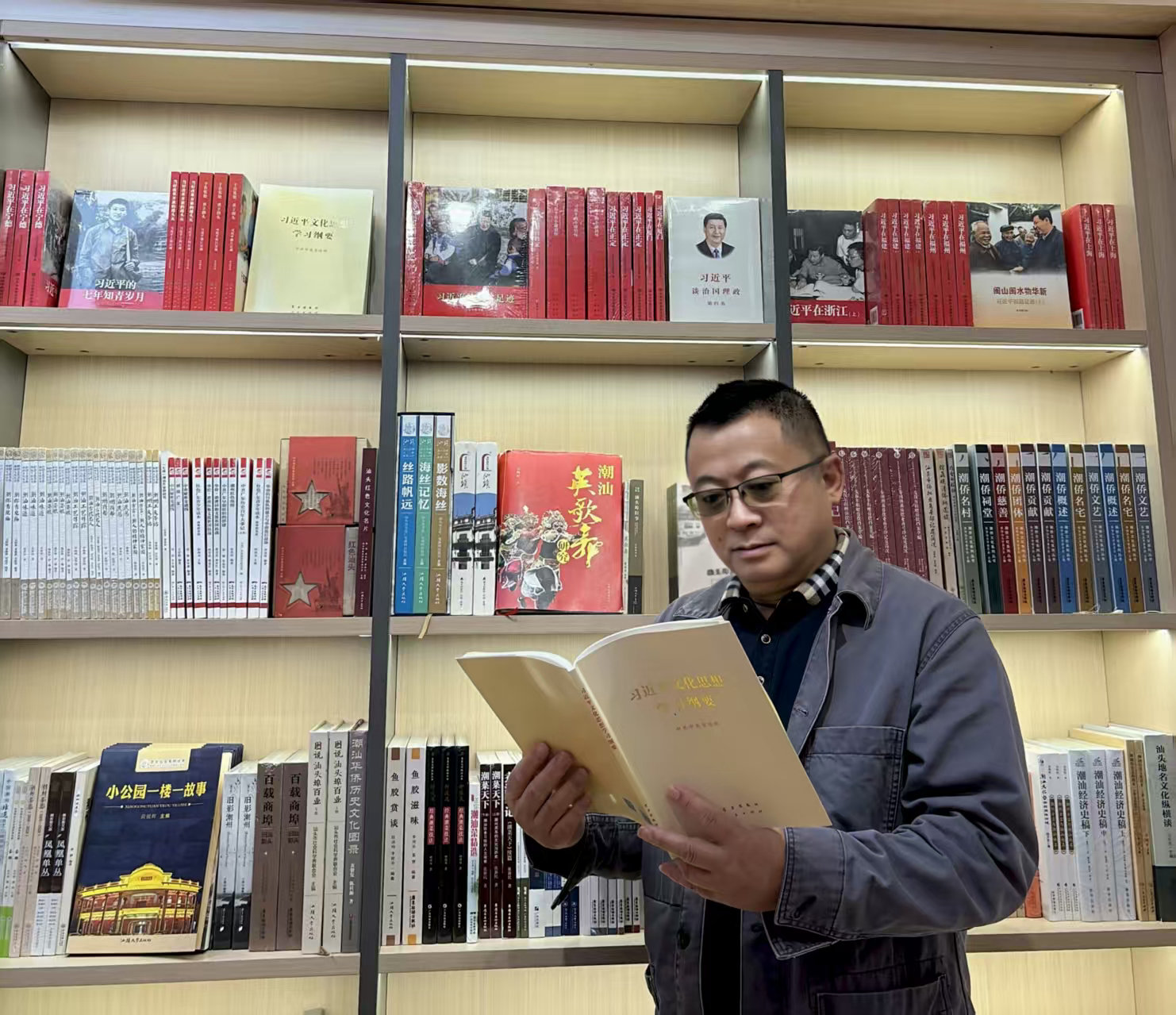庆胜利 颂国庆 | 2025当代爱国作家胡根源作品展
【 2025当代爱国作家作品展 】
--- 胡根源 ---
---★ 作 家 简 历 ★---
胡根源,海南省陵水县人。长期从事国际关系领域工作与研究。近年深耕散文创作,屡获殊荣:“妙笔生花杯”全国文学原创大赛一等奖;中国散文网第三届“三亚杯”全国文学大赛银奖及年度最美散文、第一届“春光杯”当代生态文学大赛一等奖及生态文学奖、第三届“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及大赛最美散文奖、第二届“春光杯”生态文学大赛一等奖及生态文学先锋奖;“中国年度文艺家代表作文库”特等奖并入编“作文库”;“向.未来”第二届散文、诗词全国大赛二等奖。
★★★ 作 品 展 示 ★★★
祭 奠
时间像条不停奔涌的河,卷着祖祖辈辈的故事往前淌。清明这天,我揣着心里说不出的郑重和敬畏,跟着家人踩过田埂去上坟。微风轻拂,空气中弥漫着新翻泥土的芬芳,恰似“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其实清明不只是祭祖先、念故人,更要记着那些为了民族能独立、老百姓能过好日子,拼了命抗争的先烈。这一天,我们得感激祖先养育的恩情,更不能忘了先烈们的英勇故事。把他们的精神放在心里,让它慢慢扎根发芽,这样我们往后走,才有力量。
每年清明,我都会走那条熟得不能再熟的路回乡下,跟着家里人一起扫墓祭祖。这么多年,爸妈把这些传统操持得好好的,日子久了,这些事就像刻在了家族的记忆里,透着股鲜活的劲儿。一到这时候,家里人都聚到一块儿,聊着祖先的事,把家里的文化和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祭祖的事办完,家里人就会围坐几桌,吃着菜、喝着酒,聊聊外面的新鲜事,也说说家里过去的老故事。就是在这样热闹又温馨的时刻,我偶然听到了二伯父的一些事。虽说听得不完整,可心里一下子就生出了好奇,还有说不出的敬意,也更明白家族的力量和传承有多重要。
二伯父是我爸的二哥,在我们家就是个传奇人物。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说,以前总有人在半夜看到他的身影。那时候到处都在打仗,他没半点犹豫,就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成了保家卫国的战士。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那些英勇事迹,慢慢就被岁月盖住了,没几个人知道了。
我想把这段被遗忘的历史找回来,看看当年到底藏着多少英勇和牺牲。这不只是为了敬二伯父,更是想好好追溯家族的根,传承民族的历史。
后来,在我打听二伯父胡家义——这位黎族英雄的人生故事时,有幸得到了一位老革命的帮助。这位老人家早在1939年就投身琼崖纵队,是革命队伍中一员“人小鬼大”式的猛将。当年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支队第一大队队长童光富和中共陵二区区长符开昌选派胡家义执行送情报任务的具体事宜,时任武工队三分队副队长的他直接参与了其中,可谓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他说起胡家义的事,满是深情,把二伯父为革命奉献一切的经历,讲得特别生动。
胡家义于1942年投身革命,在陵水县拾善乡抗日政府担任交通联络员。1944年底的一个夜晚,为消灭藏在孔明村尾的日军残余,他接到给部队送敌情情报的任务。然而,在前往保亭五弓大洞村部队驻地途中,不幸遭遇日军埋伏。在他的全力掩护下,同行人得以侥幸逃脱,他自己却不幸被捕。
日军对他用了各种酷刑,可他硬挺着,死都不肯说出组织的事,也没泄露送信的任务。日军急着要情报,下手更狠了,最后竟然把他开膛破肚,拿出了那张被鲜血染得看不清字的情报纸。就这样,胡家义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段历史读起来满是痛苦和牺牲,可也让我清楚看到了胡家义和无数先烈的英勇与坚韧。他们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历史里最宝贵的东西,是我们得永远记着、一代代传下去的遗产。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普通农民,可在那个到处打仗的年代,他们也没闲着。不仅偷偷掩护革命队伍行动、帮忙传递重要信件,还支持两个儿子去参加革命,默默为这事出着力。可他们到最后都不知道,儿子胡家义已经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了,甚至还被人说闲话、泼脏水。至几十年后,在他们也走了前,一直把这些委屈和嘲笑咽在肚子里,自己扛着。
经过深入的探访和细致的调查,我坚信胡家义的英勇事迹。每年清明站在祖先墓前,我心里都会涌起好多思念。可一想到二伯父为了民族大义丢了性命,到现在连他的遗骨都没找到,我就特别难受。这么多年,我们连一场正经的祭奠仪式都没法给他办。所以每次在肃穆的祭祖仪式上,我心中总会为二伯父留下一席之地。胡家义,他是一位不朽的英雄。
虽然胡家义在革命战火里的贡献,没得到太多关注和认可,但公道自在人心,总有一天他的名字会被正名。现在《琼崖红色故事》里,就详细记着他作为宁死不屈的交通员的事迹。每当我翻阅这些篇章时,心里都会又敬又感动。
虽说他的贡献难于与众多著名抗战英雄比肩,但那份牺牲精神同样耀眼。无论是这些家喻户晓的英雄,是他,皆因守护民族尊严、反抗日本侵略者,甘愿将生死置之度外。
时间过得真快,胡家义牺牲到现在已经八十年有余了。可他的英勇精神和革命信念,就像一座永远倒不了的丰碑,深深印在我们心里,会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好好往前走,把这份精神传下去。就像诗里写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墨骨忠魂:舒同书法里的家国春秋
周末闲暇,我们驱车前往澄迈县金江镇,探望从江西来琼度假的收藏家晏平兄。在他的临时会客室里,一幅舒同书法作品忽然闯入眼帘,令满室生辉。
世人多知舒同先生乃是中国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他独创的"舒体"以浑圆流转的线条,在书法领域自成一家,别具一格。殊不知,这份看似信手拈来、轻松自如的从容背后,恰是他跌宕起伏人生的生动注脚。
舒同这位从江西东乡走出的“党内一支笔”,以笔墨和文才闻名。烽火岁月里,他将笔化作武器,在宣传阵地上挥毫泼墨,写尽革命岁月的壮志豪情。
在长征路上,他用石灰调水作墨,在陡峭崖壁上写下"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墨迹未干,山风卷着标语猎猎作响,像星火落进荒山,把革命信念播撒在荒山野岭。
马背上的岁月最是颠簸。他的裤腿上总沾着墨痕---那是行军时趴在马背上写就的标语,布纹被磨得发白,倒像给裤腿绣了道褪色的花边。这支马背上的笔杆子,就这么在颠簸里记下了长征的长卷。
抗战时期的炮火里,他依旧端着笔当枪。前沿阵地的土墙上,他写的“打倒日本侵略者”比子弹还响;伤员担架旁,他用歪扭的字迹给战士写家书,墨迹未干就被眼泪洇开。
到了解放战争,他转战隐蔽战线。1948年,他以华东局社会部部长身份参与对台敌工工作,是中央钦点的台湾首任省委书记。虽因叛徒泄密折戟,可毛泽东那句“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至今仍在念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舒同的书法艺术,恰似他的革命人生,在传统与创新间开辟独特蹊径。他以颜真卿楷书为基,融入篆隶古拙与碑学雄浑,在行草间挥洒出大气磅礴的韵律。那些看似随意的"画圈",实则暗藏藏锋逆入的玄机,每一笔方圆交替间,都在追寻艺术与革命的完美平衡。启功先生"千秋翰墨一舒同"的赞誉,正是对其艺术成就最精当的注解。
在山东临沂许家崖水库大坝西端,五米高的"许家崖水库"石碑巍然矗立。遥想当年,六旬高龄的舒同亲临工地,挥毫泼墨时衣袂翻飞,笔锋与石屑齐飞。这些比人高的擘窠大字,既有水利工程的豪迈气魄,又浸透着民生关怀。当他将笔墨扎根时代土壤,艺术便升华为精神图腾,字里行间奔涌着时代的脉搏。
此刻凝视案头舒体墨迹,忽然懂得:那方折顿挫的笔画里,岂止是艺术语言?从马背指书到庙堂巨作,从情报密码到艺术丰碑,舒同用一支笔完成华丽转身。这些浸润着血与火的字迹,早已超越美学范畴,成为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当我们细品"舒体"韵味时,看到的不仅是书法大家的艺术造诣,更是一位革命者用笔墨铸就的家国春秋。
枪林弹雨中的青春:一位琼崖纵队老战士的回忆
七十七年了,总想起1948年5月那个清晨。我背着洗得发白的书包从土坯房跑出,母亲在身后扬着围裙喊我乳名"妚旺",山风把声音揉碎在篱笆墙外。我应了一声,脚底板踩着露水没回头。几天前夜里,邻村的胡仕强叔来家里串门,说有个“能识字、能跑步”的差事找我。那时的我哪会想到,这差事会把我从山村土坯房,拽进硝烟弥漫的战场。
中午,日头毒辣,我跟着交通员黎文珍大哥离开学校。脚下的山路像被晒化了一般。十四岁的我脚皮嫩,没走几里路,脚上就磨出了血泡。那时我还不知道,"解放"两个字写起来简单,要靠多少双磨破的脚、多少腔滚烫的热血才能支撑起来。
夜里摸到县委驻地岭沟仔,篝火把十几个同伴的脸映得通红。杨运民的裤脚沾着我再熟悉不过的红土,补丁摞着补丁;黄运辉手里攥着半块木薯,啃得满嘴淀粉渣。我们挤在老榕树下,听抗战老兵胡仕强说要往乐东抱由去,那里有大部队。
九所镇的硝烟
九所镇在崖县西边,像块卡在喉咙里的骨头。国民党的两个中队加地方武装三百多号人守在那儿,成了我们西进路上必须啃掉的硬茬。
1949年6月的一天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五总加强连摸黑往梅山赶,到达独岭时,露水早已将单薄的衣衫浸透,身上湿漉漉的,分不清究竟是流淌的汗水,还是这夜幕下悄然滑落的露水。班长王大哥是澄迈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他扯着嗓子喊:"小鬼头们,刺刀都给我擦亮喽!"他总把"冲锋"说成"冲崩",可真到了节骨眼上,比谁都勇猛。
敌人的机枪突然"哒哒哒"响起来,子弹带着哨音从头顶飞,像暴雨砸在野生芭蕉叶上。王大哥侧身把我往石头后推,结实的后背就挡在我身前。我看见子弹钻进他身边的泥土,溅起的红土粘在他补丁上,像开了朵腥气的花。
天蒙蒙亮时,主攻部队的枪声从三面炸开,震得山头上的碎石子往下掉。附近的老乡们扛着锄头来帮忙挖战壕,老人孩子都上手,红土混着汗珠子往下淌。就凭着这些土疙瘩堆起的掩体,我们硬生生扛住了敌军的炮火。
这仗打了四天四夜才攻下据点,王大哥的布鞋早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泥土和血水糊成一团,脚趾头从破洞里戳出来。他拍我肩膀,手心的硬茧硌得我生疼,脸上却笑开了花:"妚旺,你识字,以后班里的捷报就由你念了。"
后来听当地百姓私下叫我们"假鸟精"(九所方言),起初心里纳闷,慢慢也就懂了。胜利哪是那么光鲜的事?背后不只有激战和牺牲,还有百姓的误解,可队伍始终坚守着。就像班长王大哥,总把最后一口饭团塞给我,自己啃硬得能硌掉牙的玉米,脸上还笑得开心。
万泉河畔的月光
1949年夏天,我们五总队六团跟着大部队打石壁、龙江、阳江,这是琼纵1949年夏季军事攻势的一部分。
七月的万泉河在南孟岭下跑得欢,月光洒在龙江碉堡的铁丝网上,结的夜露像一串串碎银子。我们抬着门板往山上摸,门板上"缴枪不杀"四个大字,被露水洇得有些模糊。
午夜时分,敌人扔出的火球"轰"地在雷区炸开,幽蓝的光把战友们猫着腰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群跃动的豹子。副排长举着铁皮喇叭喊:"里头的老乡,家里的稻子该割了,老人孩子都等着呢!"
那一刻,碉堡里的枪声真的顿了顿。可也就顿了那么一下,接着又"噼里啪啦"响起来,比刚才更凶。
第三天太阳刚冒头,云梯"哐当"一声靠上围墙时,我看见守敌举着白旗慢慢走出来。他们的军装比我们的还破烂,袖口磨得能看见骨头,眼里的红血丝像爬满了虫子。
打阳江、石壁时,我们把"围点打援"和喊话劝降混着用,国民党的防线松得比泡了水的纸还快。后来每次路过万泉河,我总想起那个被火球映红的夜晚,月光下泛着白光的劝降标语,在风里哗啦作响。那些字啊,比子弹还有劲。
新宁坡的寒夜
1949年12月29日,潘江汉总队长率领五总队四、五、六团和地方武装共七个营的兵力对国民党156师张志岳部发起新宁坡战役。
当晚,我们藏在新宁坡的草丛里准备围歼敌人。十二月的山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我们穿着单衣趴在居便村的草丛里,冻得牙齿打颤,"咯咯"声在静夜里格外响。黑夜里,五团那边的枪声突然炸响,火光和敌人汽车的灯光一下子把夜空照亮。
王班长突然按住我的肩膀,声音压得低低的,又紧张又兴奋:"来了!"我看见他枪管上的白霜,在敌人露头的瞬间化成了丝丝热气。我扣扳机的手指早就冻麻了,可瞅见那些晃动的人影,一股热流"噌"地从脚底冲到天灵盖。
中午总攻的号声像炸雷,公路上的敌人跟被捅了的马蜂窝似的。我们从草丛里扑出去,刺刀在太阳底下闪着寒光,比冰棱还亮。仗打完了,我捡了件敌军的大衣披上,手往兜里一摸,摸出封皱巴巴的信。字里行间都是"娘"、"稻子"、"想家",原来他们也盼着打完仗早点回家。
王五墟的酸豆
1950年清明刚过,空气里还飘着纸钱和硝烟混在一起的怪味儿。我们往儋州王五墟赶,四天四夜没合眼,脚底的血泡将旧布鞋粘得死死的,每走一步都像有针往骨头里扎。
王五墟周边的乱坟岗成了我们埋伏的阵地。我所在的特务连,战前摸黑摸到敌人眼皮子底下,把他们的岗哨、弹药库都记在心里——那些字是用烧黑的树枝写在芭蕉叶上的,卷起来藏在裤腰里,焐得发烫。
刚夺下的据点,又被敌人的飞机炸弹炸得地动山摇。民房塌了半数,连我们靠来填肚子的酸豆树都被炸得枝桠乱飞。我带着两名战士被压制在一块墓碑后,机枪扫过来时,酸豆噼里啪啦砸在脸上,又酸又涩,谁也没心思捡。只听见副排长符天运扯着嗓子喊:"拼死守住指挥部!"
战友们倒下了,又爬起来,血顺着裤腿往地里渗,把红土染得更红。我们不仅拿下了王五墟,还顺道收复了白马井和新市,把薛岳的"伯陵防线"捅了个窟窿。后来才知道,这叫"战略牵制"——我们用脚底板和血,给渡海的大军铺了条路。看着国民党兵丢盔卸甲地跑,我忽然觉得,海南岛的天亮越来越近了。
澄迈的最后一程
王五墟的硝烟还没散,澄迈的福山、美亭又响起了枪炮声。四月的太阳毒得像要把人烤化,我们班作为尖兵走在最前面。突然听见班长"哎哟"一声,直挺挺倒在地上——冷枪从树后打来,子弹打中了他。
我那时是二排副班长,负责断后,赶紧大喊"卧倒",眼睁睁看着子弹在身边的泥土里钻出小坑。后继部队赶上来时,我们已经打退了三波敌人。班长拉着我的手,儋州口音混着血沫:"妚旺,带着弟兄们...跟上队伍..."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美亭、黄竹战役后,我们跟着渡海部队追残敌。草鞋磨破了,就光着脚在红泥土路上跑,血印子一路滴过去。直到看见解放军的红旗插上山顶,红得像团火,我才敢相信,打了两年的进攻仗,我们真的赢了。
海南解放后,我被编进野战军,转战广东、东北、福建前线等地一大圈后,因伤退役。正是“去时青衿正少年,归时年轮近而立”。
七十多年过去,海南岛的椰树绿了一茬又一茬。当年青涩的小战士,如今已是白发老人。每次走过万泉河,踏上新宁坡土地,战火中的青春记忆就如潮水般涌来。战友们穿着单衣在冬夜冲锋的身影、黎明时用酸豆充饥的场景、倒下又立刻爬起来冲锋的弟兄们……这些画面总在提醒:今日的安宁和平,是无数像班长、副排长那样的战士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份牺牲与奉献,我们永远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