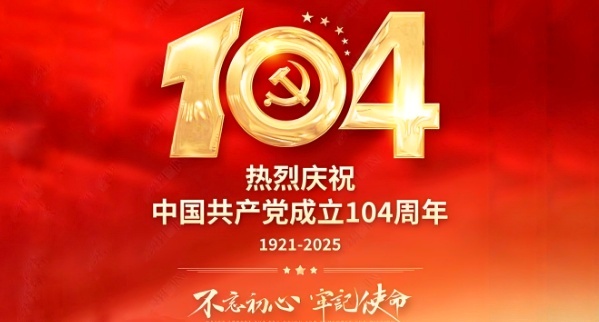【党庆特刊丨特别推荐建党104周年当代作家:徐揭阳】
特别推荐建党104周年当代作家
丨徐揭阳丨
作 家 简 历
★ 作 品 展 示 ★
观 瀑
苍宇白云献哈达,飞流银练腾浪花。深情拥抱跃嶙峋,一路狂啸震天涯。一个人去旅行,前往贵州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自治县看瀑布。想像中,那天外来客,是否曾在张果老的榕树下唾涎做了一个美梦……从遥远的天边仙仙而来,归心似箭,飘飘欲仙,欲断魂。一瞥惊鸿,纵身一跃扑向梦中浪漫怀抱……淅淅沥沥,烟雨朦胧,雾霭氤氲,袅袅升腾。滋润着苍翠,青山如黛。跟随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越沉睡的历史长廊。看见,在波澜壮阔的飞流直下的你,云雾缭绕,落霞孤鹜,灵秀清欢。只因,喀斯特地貌,因地质运动而分裂如此形态。时光如梭,为圆梦境,追寻、跨越时空之念。赤裸裸、净身飞跃断崖式迷宫。畅游爱河,翻江倒海……行至烟雨前,水珠妖娆,细细无声,清凉舒爽,乃人间仙阁,世外桃源也。爱,孕育于新的生命。沉积于巨厚碳酸盐岩,夹少量薄层状云灰岩中。晚更新世时期由“宽谷期”向“狭谷期”演化成地上河流。后因“喜马拉雅运动”多次间歇抬升。导致河流侵蚀,溶蚀下切形成“裂点”“裂隙”,溶洞、暗河,发育成熟。喀斯貌洞顶,逐渐坍塌,瀑布终于呈现,至今约五万年时光。独自静好,锁在深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潺潺白浪,滚滚向前。
孤芳自赏,未曾被人间所阅。
十八世纪后,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游历到此。巧遇仙境,“……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厉,所谓珠帘钩不卷,飞练挂遥峰’,但不足以拟其壮也”。才让后来者,认识它的惊艳和美的壮观。不管是沉睡千年亿万年的“黄果树瀑布”也好,还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也罢。都是:天仙下凡飞细雨,雷鸣怒吼万重烟……那怕是枯水期,偃旗息鼓,歇息,也不忘铺展于整个岩壁之上,也更不失其“阔而大”的宏伟气势。生生息息,磅礴恢宏,深邃浩瀚,溅珠飞霞。传述着山水之恋,缠缠绵绵,经久不息……苍穹白云朵朵,瞬间山谷流淌,烟雨滋润,绿植翠嫩,泉浆玉液,如胶似漆,心心相恋……好一副山水之画,大自然的馈赠。国人之福,世人之福也。静谧之处,独自静想:吾,如苍海一粟,甚是渺小,只有这大自然,激情澎湃,遥相呐喊,追光而灿,迎光而烂,才是永恒!瀑布之大,终将汇入江海。人生之路,虽岁月蹉跎,历尽坎坷,吾,仍感觉幸福颇多。
感觉每一滴跳跃水珠,浪花,仿佛能听懂它们在䜣说;日月星晨,沧海桑田,人间悠欢……
花城里的北京路
同学跟我约好,明天再往北京路逛逛。
当第一缕阳光冉冉升起,晨雾还在懒悠悠地卸去睡装时,我们挤上了地铁,向着花城里的北京路奔去。我心生诧异,别名花城的广州为什么会有北京路呢?
哦,广州的北京路,是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区代名词。与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武汉的汉正街一样。
但凡来广州的商旅,没有不到北京路去的。这条充满传奇、历史悠久,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熟得不能再熟悉的北京路,却藏有许多的沧桑故事。
两千多年前的公元204年,秦朝大将赵佗在岭南三郡的基础上,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这就奠定了广州在岭南的中心城市地位,也有了早期的北京路雏形。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南海郡尉任嚣在北京路一带筑番禺城。作为南海郡的郡治,这是广州城建城之始。
从南越国时期,再到唐代、南汉、宋元、明清、民国等五个历史时期,跨度千余年之久。在唐代以前,北京路一带,均是低洼的河涌地。唐朝时,人们开始将低洼地堆土,填平,筑路,建楼。古代的先民,以勤劳为本,努力建造自己的家园,至明清时期,城市布局已初步形成。
北京路古道遗址的玻璃栈道下,有古代的砂、岩、土砖、古路面等,清晰可见。这里至今保留着从秦、汉、晋、南朝、隋唐、南汉、宋元明清到民国的遗址。那灰色的土,陈旧的路,斑驳的断墙残壁,无一不在宣泄着久远的过往,展现着历史的沧桑,演绎着时代变迁的厚重烙印。
在遗存千年古城遗址的北京路上,还耸立着一座明代拱北楼。拱北楼上有一座元代的铜漏壶,传说百年精准无误。这座拱北楼,因有两个拱门而得名“双门底”。在清朝时,这条街叫“双门底”,以前不叫路,都是以门牌号叫街。“双门底”街以西湖路为界,分上街和下街。上街位于今北京路以北,下街一直延伸到永汉电影院所在地。
在这里曾有一座名为“大南门”的城门楼,是广州内城的一部分,城墙位置就在今天的大南路和文明路。
明洪武九年(1376年)撤销中书省,以后陆续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是最高级别的省级行政机构,在明清两代近六百年统治中,广东布政司署一直位于南越国宫署遗址一带的今广东省财政厅所在地。
双门底下街,大南门又称正南门,为明初广州城扩城时所开。据明万历《广东通志》记载,“月城城名延三十八,上俱建层楼下辟三门”。民国拆墙时所毁。今存以其命名的大南路。
从城防图、无字码头进,叫永清门——大南门——南门直街。在清代,“双门底”就是商业活动中心,因此有“双门底”卖猫——假装的歇后语。
至今,仍在双门底经营的是历史悠久的陈李剂药厂。它的前身是陈李剂杏和堂,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其辅面在今“银座”附近,经历了近五百年,是这条北京路的历史见证。
古老的北京路啊,沉甸了岁月年轮的故事。它虽没有古战场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也曾激荡着烽火狼烟的商海沉浮。
从最早的钱币制造,到1757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作为唯一官方通商口岸的全球金融中心。千年商都的辉煌,文脉绵长。
从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的两千多年来,广州的官衙基本都设在北京路以内。它不仅有着悠久历史渊源,并且一直维持着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是广州古代延续到现在最古老的城市中轴线,是记载广州两千多年发展的“无字史书”。
在这条中轴线上,历朝历代就是商贾活动中心。民国时为拓宽拆掉此门,改为永汉路。永汉路,是为了纪念第一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上世纪四十年代,又恢复永清路,直到1966年正式命名为北京路。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那跌宕起伏的商海鏖战,正是广州先民崛起的希望之光,在这条古老的北京路上述说着流年往事。
广州,在风云际会、商海沉浮的历史变迁中,其中心城区和中心商业区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这里,不仅创造了中国国内外城市建设史上罕见奇观,也造就了广州灿烂辉煌的历史和商业文明。
触摸北京路的历史长廊,俯瞰繁荣昌盛的千年动脉,感知一代又一代广州先民的勤劳智慧。今天在新时代召唤下,广州人仍然“英雄花开英雄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将国际大都市的家园打造得更加壮观。
龙 舟 赛
一场暴雨,将锦江河灌醉,把两岸青山染翠。
深沉而宁静的江面,烟雾缭绕,纷纷扬扬播撒着清辉,笑迎龙舟赛事的到来。
来来往往,喧喧嚷嚷的人群,早早守在沿河两旁。年轻的姑娘穿上漂亮衣裳,在为村里龙舟呐喊助威的同时,特别欣赏,那些散发着雄性荷尔蒙,胸背肌肉强悍的后生汉子。
江河里那些挥桨划撸的汉子们,理头苦干的同时,总想着岸上该有多少迷人姑娘的眼神,在流光辗转注视着自己伟岸雄起的青春身躯,真希望在这场热闹的龙舟赛里,被丘比特的金箭射中。
爷爷奶奶们,悠哉悠哉,牵着孙孙宝宝,搬来小小板凳,围观在龙舟赛的河岸两旁。啦啦队员们,紧密锣鼓般,热情拥簇着,随时准备首,引吭,呐喊,助威。团团鞭炮,码放在岸边石墩上,只等龙舟比赛的第一声哨响。
寂静的山野,沸腾起来,两艘龙舟,在一声哨响后,似离弦之箭,在整齐的划桨声中,拨开水面,乘风破浪,飞溅的浪花,似一道道孤线与粼粼波光交相辉映。
突然,人群中一声炸响“破敌书”,啦啦队齐声“加油!”“破敌书”“加油!”又一震耳欲聋“红冬谭”“加油!”“红冬谭”“加油!”
破敌书龙舟队,有位汉子小舒。身材魁梧,肌肉结实,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透着质朴与强悍。从小在河边长大,对龙舟赛充满向往。在他眼里,龙舟赛不仅是一场竞技,更是一种对祖辈的传承和敬童。
小舒和他的队友们,对于扒龙船,都有一种深深地热爱和执着的眷恋。他们在心里,都铆足了劲火,一定要扒赢龙舟赛,扒赢对方。
由于青壮年劳力,长年在外打工。人数不够,在外打工的人临时赶回来,扒几天船,训练几天。天刚放言,开始苦练,风里雨里,脚泡在水里,泡烂了脚趾,不怕,累了,苦了也不怕,咱有破敌书不屈不挠的吃苦精神。那种烙在骨子里的不服输的拼搏精神。小舒虽然住在高村,但每天起早贪黑,早去晚归,坚持训练。一身黝黑黝黑,背脊上一道道黑黑的痕印。真像一个吉普赛黑人,有人唤他黑陶俑。小舒不光积极投入训练,还特别怀念老一辈人说起的那些久远的传说……
在很久以前,破敌书只有两户人家。传说,一县太爷从贵州安顺告老还乡,途经舒家村滩上。船行至此,只见两岸青山巍峨耸立,峰峦叠嶂,云雾缭绕。这时,突然狂风大作,飞鸟大叫。船家只好下船躲避风浪,当行走至破敌书处。沿途风景不错,山请水秀,看好这个地方。于是决定留下,在这里安家扎寨。官员一行随从,在这里修祠堂,供神龛,安了家。那时,这地方发大水,淹不着。再大的水,只涨到祠堂门口就停住了。天旱不着,水淹不到,是上天的保佑,真是一快风水宝地啊。人也发得快,后来发展了一两百户人家。
民国时期,舒兴宇就读于黄埔军校。军校毕业后从军,后被收编,告老还乡回到了破敌书。舒兴宇的儿子,随国民党军开往台湾,终老台湾。
传说,有位老太公,从少年起开始科举考试。一至考到83岁,还在考,这下感动了当朝皇帝。皇帝当即下了一道圣旨,封他为县令御室官员,以示对这种不屈不挠精神的赞扬。相传明朝年间,一将军因剿匪战败,路经“坡上舒”,准备在外安营扎寨休整。族长得知原委,即要求头领带队入住村中,并答应为将军筹集粮饷,又派人以买纸为由,打探匪情。三个月后,将军带兵征战,一举剿灭匪窝。为表示感恩与纪念胜利,征得族长同意,将军将“坡上舒”改名为“破敌舒”。
二十世纪中期,易名为“破敌墟”和“破敌圩”。至七八十年代,再次职名“破敌书”,一直沿用至今。那祠堂就在现今舒家村学校处。以上传说,虽年代久远难以考证,但破敌书人不屈不挠的刻苦精神,代代相传。穿越时空逆境,从古延续至今。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破敌书先后有八十名学子,考入各大中专院校。2012年,2024年,舒强,舒嘉琪分别考入北京大学,对村里,县里,不得不说是一个震撼。
龙舟竞技,在舒家村,曾经间隔了四,五十年。五八年时,邻村人笑话;破敌书人恐怕不会扒龙船?也没有舵把子艄公。追上去五十年,破敌书人是扒过龙船的,也有好的掌航艄公。为了争口气,他们自费凑钱,打造船只,起早贪黑,天天苦练。风里雨里,是那种烙在骨子里的蛮劲,1是那种不服输,不认输的气节坚定。
5月29日,江口赛区第一轮第一篙,破敌书跟红冬谭比。破敌书没发挥好,落在红冬谭后面。“宁呜而死,不默而生”,更有屈原的“诚即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虽然落在了后面,但并未阻挡龙舟健儿的决心。“宁输一丘田,不输一箭船”的信念,是烙在骨子里的1倔强与拼搏精神。第二篙,他们个个铆足了劲火。小舒与队友们配合默契,他们的桨整齐地落下,又迅速地抬起,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
两支队伍,就像两条在江面上飞驰的巨龙,向着终点奋勇前进。
破敌书队,不甘示弱,突然加速,他们逐渐驶出前沿,两支队伍的差距慢慢拉开。观众们的呐喊声,也越来越响亮。他们的加油声,仿佛为龙舟注入了新的力量。队友们的手臂因长时间的划浆酸痛不已,但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赢得比赛,传承破敌书精神。
在集体努力划桨下,前行的船支,如脱缰的烈马……
在最后的冲刺阶段,破敌书队,最终先于红冬潭队到达终点。桡手们汗水湿透了衣衫,紧绷着的弦,终于放下了,提到嗓子眼的那口气终于松懈了。长吁了一口气,脊背在阳光里绷成铜色的弧,每一次俯身,都让龙舟在水面犁出箭簇般的浪痕。船尾的浪花,又似“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路,此刻正托着木舟颠簸,桡手们每一次挥桨,都像是在打捞沉在河底的诗篇。
小舒坐在龙舟上,在阵阵鞭炮声和浓烟袅袅中,望着欢呼的人群,心中充满了自豪。他知道这场胜利不仅属于他们,更属于破敌书的每一个人,属于那些传承了百年的精神和文化。在这一刻,龙舟的韵律与破敌书的历史,人们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激昂的乐章,也预示着这种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精神,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传承下去,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破敌书人,在生活的长河中勇往直前。
桡手们捧起河水,洗去的是汗渍,洗不淡的是刻进骨血的印记。当孩童追着龙舟奔跑,当老人哼起悠扬的歌声时,小舒忽然懂了,那些关于县太爷安家的传说,老太公的执念,黄埔军校生的背影,从来不是躺在故纸堆里的故事,而是桨叶破水时的震额,是号子喊破云霄的铿锵。
龙舟靠岸时,在破敌书,红冬潭及所有参加赛龙舟的队员们的对视里,没有胜负,没有输赢,只有江水浸透过的默契。就像破敌书与红冬潭的竞渡,从来不是敌意的对峙————你追我赶的桨声里,藏着对“不服输”最赤诚的致敬。当桡手们用河水互泼笑闹时,忽然明白,竞渡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超越对手,而是超越昨天的自己。让破敌书不服输,不认输的倔强,在年轻的血脉里,长出新的年轮。
晚风掀开粽叶的青香,那些未散的号子声,是江水写下的诗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魂,在每一次挥桨里复活,“长太息以掩涕”的悲悯,在每一朵浪花里重生。破敌书的祖辈或许不知道,他们打造出来的龙舟,划出来的从来不是简单的水痕,而是千万人用血肉之躯,在时光长河里,为屈原续写的永不沉默的《离骚》。
赛龙舟的队伍散尽,那些沉在河底的诗篇,随着桨声起伏,随波漂向远方————漂向每个追着龙舟奔跑的孩童。漂向每个在晨光里挥桨的后生,漂向千年后仍会在端午时节,为一声号子热血喷张的人们。
原来,有些东西,早就藏在这一桨一舵的起伏里,藏在风里,水里,藏在千年未改的端午晨光里。
原来,龙舟韵里藏着的,从来不止是水花与鼓声,而是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的关于“不服输,不低头,不忘记”的,湿漉鹿的,带着河水气息的千年未改的端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