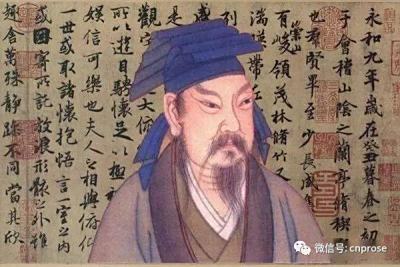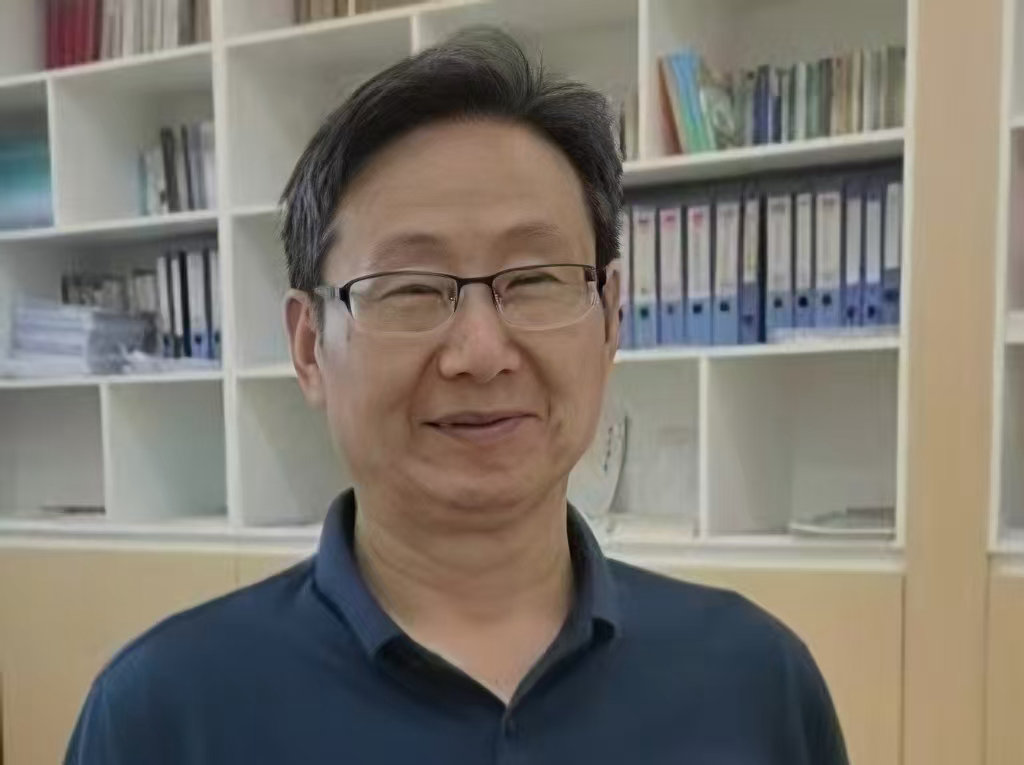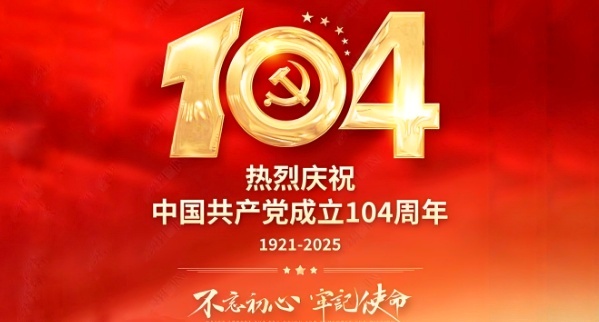【党庆特刊丨特别推荐建党104周年当代作家:王玉才】
特别推荐建党104周年当代作家
丨王玉才丨
作 家 简 历
★ 作 品 展 示 ★
逃出的旮旯回头满阳光
我出生的地方叫大淤尖,是黄河夺淮、泥沙堆积而淤长到海中的一块尖角。小时候,和伙伴们赶海、跑滩,就在这个尖角上,向北跑到黄河故道入海口,向南跑到灌溉总渠入海口。在这个区间,听惯了波涛的高吟,看惯了鸥鹭的低翔。这里曾经很遥远,很偏僻,从我知事起,就听说很多人家都规划着逃离。
这片土地在成陆后的几百年间,人稀烟少,难进难出。如果不是明初“洪武赶散”,人口北漂,逐年向海边挤压流动;如果不是三年自然灾害,政府动员人民去垦荒,这里也许至今还是芦苇荡、盐蒿丛,獐猫鹿兔的栖息地。
实际上,在伟大领袖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之前,这里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住在淮河的尾巴上,因为淮河已经改道入江了。只知道北面有条废黄河,长满芦苇,有人在那里钓过几斤重的珍奇大黄鳝;只知道大海的波涛,年年侵蚀着沙滩,一片片绿洲淹没到巨浪之中,每年七八月份都会提心吊胆,生怕重演一九三九年中元节那场海啸;只知道隔两年就会发洪水,暴雨漫天,一地汪洋,床肚捕鱼,灶堂捉蟹。人们很少外出,也不去寻祖,四时八节,只置办些饭菜,在地上划个圈,烧些纸钱,便算不忘自己的根了。我记得我家每次要供八位祖宗,八碗饭、八双筷子,分四面摆上桌子,边烧纸边说些鬼话,纸烧结束,男丁从长至幼每人作三个揖,就收了桌子,自己吃饭。供祭的时候,老太太如果在,会如侍者般立在桌旁,盯着看,看到碗里冒着热气,便说,老亡人吃得快活呢,热气哈哈的。我们读了书之后,便由起初的敬畏渐渐转为窃笑。
治理淮河是新中国送到这个偏僻地方的第一缕阳光,使这里的人们感知了外面的世界,找到了自己在淮河尾闾的方位。
但淮河修通后,特别是三条八滩渠开挖之后,我家夹在中、北八滩渠之间,这里成了真正的旮旯,成了行洪道,交通更难通。虽没了漫天洪水之患,却由于水系变化,夏天积水反而更多了,后来知道叫“客水倒灌”。在我上小学时,每到雨季就不得不光着脚走。女生不愿光脚,便要脱几次鞋蹚水,有的因此辍学了。大人赶集都把鞋子系在扁担拽子上,一悠一悠的。村里有一个漏头户,买了一辆自行车,两个手把裹着大红布,平时就架在床上,赶集时先扛着走,上了大路才舍得骑。如果遭了雨,则一路都被车骑着。
十岁,我第一次随父亲外出。那是临近过年的一天,我们吃了早饭,背着太阳,沿着沟边小路,走到河边小路,走到堆边小路;又顶着太阳,走到日头偏西,腹中辘辘,两脚疼痛,方到三伯父家。休息两日,又起了个大早,来到渡口,买票等待。不知等了多长时间,才排队挤上一条蓝色的铁壳船,在几个戴红袖章的人吆喝下,钻进船舱。还没坐稳,便听到“突突突”的响声,接着听到“呜——”的长鸣,接着河水动起来,船身离开岸边,向前行进。从客舱的小窗向外看,一条斜着的波浪从船头连到河岸,冲得岸边回应着船头,一起发出“哗哗”的响声。鸭子在捞食,波浪过来,抬头张望;波浪过去,又蹶起屁股接着捞它的食。夜深了,父亲催我眯一会儿,我新奇地一直望着外面黑魆魆的天边,影影绰绰的房屋、树干,零星的灯光。天快亮的时候,我们下了船,到的地方叫溱潼,父亲的老家。这次外出,连休息一共用了四天一夜。
就在这样偏僻的地方,新中国按伟大领袖的号召,将学校办到了村,办到了农民的家门口,先有一至三年级,后有四至五年级,又增加了带帽子初中。这是又一缕阳光,为这个旮旯带来了光明。我和我的同龄人成为获益者,其间部分人因此改变命运,离乡进城。
到我进县城时,这里除了一条离家十几里的战备公路,大部分地方毅然是闭塞的天涯海角。那一年,我有了小孩,要回家报喜,正巧单位领导要去海边办事,便同意我搭车去。在半路上,我下了车,并约定下午四点到海堤闸口集中。我急急地吃了中饭,父亲非要我带一条十几斤重的大拉瓜回我的小家。我扛着走了三里多,早早地到闸口等。四点过了,五点过了,六点七点又过了,闸上亮起两盏昏黄的灯,惨白的半月挂在高空。这时,闸管所的人吃了晚饭出来散步,突然发现有人在闸上来回走,便警觉起来,前来盘问。我告知原由,他们将信将疑,旋即留一人看着我,一人去报告所长;所长又来盘问,又回去打电话证实;直到九点左右,才告知我,车子下午两点多就因急事回去了。海风吹乱了我的头发,吹凉了我的衣衫,吹酸了我的鼻头。我扛起拉瓜往回走。走过一处坟地时,隐隐绰绰的坟头,似乎就是耕田的张大爷、剃头的沈大爷在看着我。我实在无力了,扔了拉瓜,目不斜视地走过。
这个旮旯也极少有人去,难得有亲戚上门。喜鹊不少,却不容易看见它们飞到屋后的树上大叫报喜。因为偏僻,乡里分工干部多不愿到这里来。印象中,只有一个嘴有些歪的干部,在这里真正住过几天,倒是很平易,远远地看见妇女就说笑话,逗得女人们咯咯的,她们私下都亲切地叫他“殷小歪”。他在一户农家带伙,中午吃白米饭,饭头上还盖着洋葱炒鸡蛋,便吸引很多人的目光,更激发起人们走出去的欲望。这人很会说,讲形势一套一套的。
三十年前,在我进城工作时间不长,立足未稳,还无力赡养老人的时候,母亲受到上学、参军、打工、经商股股逃离风的影响,再不能忍受这里的偏僻贫困,生怕早晚生病得不到及时施救,迫不急待地拆了房子,卖了所能卖的,将屋基田、自留田等合计五六亩,一股脑地以每年三百元的价钱,包给邻居种植,住到了县城我的身边,直至今天。
今天,沿海战略,沿江战略,上海经济圈,陇海经济带,淮河经济带,一缕缕阳光集束高照,旮旯渐成都市,大淤尖早已不再遥远,不再偏僻。
打开世界地图,它就在那片最大的蓝海西北,在“中国·滨海港”南边那个熟悉的角落。
一马平川的冲积平原上,水网密布,纤陌纵横。春天,柳岸花堤;秋季,果香阵阵。
大港建成,为祖国站岗放哨的边陲变成开放发展的前沿。央企落户,全国规模最大的LNG储备基地建成,百里海堤风光带蓝图绘就。千里迢迢的人们赶来休闲观光。海湾成了网红打卡地。滩涂成为开发区,片片腾起热浪。淮河入海水道建成二级航道,百舸争流。
那里已有高铁、高速,陆路、水路、空路,路路通达。
淮尾,曾在深闺人不识,如今,渐出海角展新容。
梦中,我又回到了我的老屋,我的衣胞之地,熟悉的涛声,熟悉的鸥鸣,还有童年的玩伴。
(初稿写于2024年5月,父母还在的时候)
拐 磨
你知道拐磨吗?拐过的,都应该是老人了。拐磨是我记忆中最辛苦的劳作,没有之一。有人说写文章爬格子是世间最苦的差事,香烟不离嘴,钢笔不下水;踱步声音长,文字出来短,劳神,难产,但比较起来,我还是觉得拐磨更辛苦,比挑担推车还辛苦。
拐磨辛苦,倒不完全是费力,主要是无趣,烦心,晕头。
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没有驴子,拐磨都是靠人工。有磨子的人家也很少,村庄里十几户人家只有左大爷家有一台磨子,是搬家带过来的。那个磨子很壮实,不像一般小磨子倒浪阔机的,用力就怕散架。磨架子都是由很粗的木头做的。磨盘由两爿青石组成,上盘有下盘两个厚。那磨担也是笔直的,很粗壮。我第一次去拉拉看,竟没拉动,惹得大人一阵笑。左大爷家磨子很忙,一年到头叽咕叽咕地转不停,尤其阴雨变天,过年过节,越发的忙。到他家磨粮食都要排队,有时几天排不上,家里断了顿,便向已磨出来的人家借三两升桶先吃,等自家磨下来再还回去。父亲最怕拐磨,每拐一次磨便像生了一场病,头晕,呕吐,睡半天不能还魂。我们兄妹几个还小,看着也帮不上忙。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庄子上有户人家搬走了,他家有个小磨子便卖给我家。父亲特地搭了个小锅屋,将它安在锅台的边上,从此,拐磨成了母亲和我们的事,直至村里有了粮食加工厂,磨子成为古董。
记得第一次磨的是玉米。母亲一手拽着磨担头,一手捏着玉米粒,我两手抓着磨担柄,将磨子推拉得飞快,弟妹们挤在旁边看,跃跃欲试,诵着“拐磨拐,请舅奶,舅奶不在家,请老丫,老丫不会走,请黄狗,黄狗会咬人,一家吃不成”的童谣,嘻嘻哈哈地欢笑。拥有自家的磨子,不用排队,不用仰人鼻息,不用暖死也要穿着衣服,想什么时候拐就什么时候拐,想拐多少就拐多少,全家人都洋溢在享有自由支配权的兴奋之中。但不一会儿,他们就看够了,都跑出去玩了。母亲一个劲地说,慢点慢点,磨子飞起来磨不碎。我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毅然轻快地推拉着。
看着磨盘一圈一圈从眼前转动,玉米一粒一粒从磨眼喂进,糈子一点一点从磨缝吐出,小箢里的玉米却迟迟不见少,便催母亲多放点,不要每圈只放一、两粒,母亲愤道:多放磨不碎,还要重磨,不一样吗?我没话说了,继续盯着磨盘一圈一圈地转。后背的汗凉了,觉得口渴起来,便要停下来喝水。一会儿,又觉得磨担吊太高了,母亲又停下来,将吊磨担的绳子放长些。我头晕起来,外面清脆的鸟鸣,耳畔单调的磨声,形成强烈的反差。母亲用力地拉着磨担头,我机械地扶着磨担柄,推着,拉着,转着,叽咕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在我连篇哈欠中终于告一段落。
我第一次体会了拐磨的辛苦。尽管辛苦,磨还是要拐的,不拐便没饭吃。拐磨成了全家最大的负担。二弟、三妹都试过了,热情只在一瞬间。尤其是三妹,完整遗传了父亲的基因,一拐磨就抱着头干呕。母亲有时生气说,还不如到左家大磨上拐呢,尽耽误工。
过两年,我们长大些,我便负责带磨担头,二弟、三妹两人一左一右摽磨担。那是个星期天的早上,正是开镰收麦时,母亲上工前拿了半笆斗大麦仁出来,叫我们拐,并说中午不拐完不准吃饭。我们一个劲叫苦,可母亲扬长而去了。我们拐一阵,歇一阵;磨子飞一阵,爬一阵。母亲放工回来,我们还剩三分之一没拐,便很生气。她一边生火做饭,一边不停数落我们,偏说我们玩了,我们已无力争辩。饭香飘进我们的鼻子,肚子似乎比磨子还响。父亲苦着脸,说先吃口饭再拐吧。母亲说:不行!下午还要拐玉米!今天不拐完就别想吃饭!
磨子叽咕叽咕地还响着,但越发地无力了。不知转了多少圈,母亲又送来一小箢子玉米,说:先去吃中饭吧!这是下午任务,不拐完,晚饭也没得吃。磨子停下来,我的左膀子已抬不动,二弟瞪着眼不知向谁看,三妹托着头蹲在地上干呕。这一天磨得我们没了一点脾气,磨得我们见磨色变,很长一段时间,一想到磨子便觉得天在转。后来事实证明,母亲是对的。那一年雨水特别多,麦子收回来就堆在屋里,一个多月动不了磨子,邻居有人家不得已只能煮大麦丸子吃。
但是,临近小满,母亲吩咐可以拐稔稔了,我们的精神便随之振奋起来。我家当时还种有两张席子大的一块元麦,元麦拐稔稔是最好的。但一年只能拐-次,一次只能拐一小盘子,因为拐稔稔很费麦,一小盘子要废一大片麦。我们便跳跃去掐麦穗,搓麦皮,筛出麦仁来上磨拐。一把喂进磨眼,清香满室,瞬间赶走磨房霉味,使人兴奋,于是磨子转得更快更圆。
那年,为了筹集我们的学费,父母商量了几夜,决定借钱去街上买二十斤豆子,做一作豆腐卖卖。父亲起了大早,豆子一买回来就浸泡到水中。第二天又起了大早,开始磨豆浆。磨一遍,将浆晃下来;又磨一遍,又将浆晃下来。紧紧忙忙一直忙到下午,终于弄好,将豆浆舀进锅里煮。煮豆浆要专人站锅口看,一不留神,便会四面潽出,直至锅中潽净。潽而不溢便是开了,一瓢一瓢舀到缸里,盖好保温,又煮第二锅。大概煮了三锅,全煮完了。母亲将缸盖挪开一点,透出三分之一缸口,开始点盐卤,边用木柄长勺子搅动豆浆,边将监卤均匀滴入其中。豆浆里便看到豆腐脑。豆腐脑由小变大,由嫩变老,便不再点卤,又养一会儿,便舀出来上包,沥水,压实,切块,便成了豆腐块,可以挑出去卖,换钱。可是,压实的时候,父亲过早地搬了磨子的上扇压在上面,一下子将豆腐包压炸了,豆腐喷了一场地。父亲呆了,低着头。母亲转身去抹眼泪。邻居看到了,过来劝慰几句,摇头走了。不知过了多久,父亲才缓过神来,将磨子搬开,将剩余的重新包好,压实。小狗闻见香味,过走舔食,被狠狠踹了一脚,昂昂昂地躲进草堆,远远地望。
一日,有石匠挑着担子沿路喊凿磨子。母亲请人家来看看,石匠一看,磨牙子都磨平了。一番讨价还价,石匠将两爿磨盘搬到外面,磨牙朝上,原来以磨脐为中心,有一条一条向外辐射的楞子,粮食就是从楞子沟里磨碎挤出来的。石匠用铁錾子顺着楞子沟一行一行地凿一遍,楞子更高了,楞沟更深了。新凿的磨盘要先拐糠,拐很多的糠,把碎石子磨干净才能拐粮食,否则,石子进到粮食里会磞坏牙。我有两颗牙就是饭里的石子磞坏的。我观察发现,人吃饭有两种,一种像我这样的,每口必嚼,不嚼咽不下去;一种如家属,好像什么都不用嚼,到嘴到肚。我常吃到石子,她从来没吃到过。孩子拉了巴巴,她捂着嘴往外跑,喊道:快来快来,我喉咙浅。我便嘲笑:你连石头都吞得下去,这点巴巴还能卡住你?她便捏紧拳头作势要打我,后来果然卡不住了。她是小街上的人,从小吃供应粮,只知道拿口袋排队买米,不知道拐磨,真连林黛玉都不如,印象中黛玉尚知道驴子拉磨呢!写下这句话,我突然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磨眼里:林黛玉何曾知道驴子拉磨?我赶紧百度一下印象来源,原来是有人说《红楼梦》第五十回林黛玉出过一个谜语:“騄駬何劳缚紫绳?驰城逐堑势狰狞。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说其谜底就是小毛驴儿拉磨。幸亏我早年读过《红楼梦》,又将第五十回从头到尾读一遍,方知被误导了。原文虽未交代谜底,但借宝钗和众人口已说明了谜底类别。宝钗道:“这些虽好,不合老太太的意思,不如作些浅近的物儿,大家雅俗共赏才好。”众人都道:“也要作些浅近的俗物才是。”就是说,宝黛钗的谜底都是俗物而已,黛玉出的谜,谜底其实就是他们常见的皮影,那是什么毛驴拉磨。有点委屈老婆大人了。
思绪如流水,一不小心就从磨子流到了林黛玉,亦如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一不小心就从石器时代进入了现代化。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身边的一切,日夜在变,可以说是几千年来生活变化最快的时光。磨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据说,最早的磨子由石磨盘和石磨棒组成的,这种原始的粮食加工工具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就已经出现,到了汉代才被称为磨子,到晋代才发明了用水作为动力的水磨。后来,有了各种各样的磨子,但终究是石头工具。只有到了二十世纪后期才一下子有了机械、电力驱动的钢磨,人们终于从辛苦的拐磨中解放出来。
像人类会忽然出现个浑身长毛的人猴一样,生活也会时不时忽然返祖一下。在拐磨渐渐淡出人们视野,成为回忆的时候,近期又兴起了用石磨,并说石磨豆浆就是不一样。不过,这与石器时代的磨子完全不一样了,这是电动的石磨。祁愿人类脑回路正常些,不要忽然说人力拐出来的豆浆比电动磨出来的更好,而使人们重去摽磨担,那可真的很辛苦啊!
楝树的念想
退休后,去乡下宅院栽树,悄悄栽了两棵楝树。家人、外人看到都不理解。家属直接要拔掉,邻居也说,屋前屋后不宜栽苦树。我坚持着,并时不时去看上几眼。
楝树,一种生长在农村的极普通的杂树。我原以为只有我对这种树怀有特殊的感情,没想到今天看到一篇微文,题目竟是《我的眷眷“楝”情》。再一搜,有楝树情结的人还真不少。印象较深的是辛叶的楝树枣子砸新娘,想不通怎么会有这么暴力的风俗,还专门挑裸露的脸、脖子、手背砸,一疼一串人;朱美玲的打楝树枣子卖钱,母亲为了安慰小女儿,竟从哥哥的篮子里偷些过来,如此甜蜜的“偏心”。
我没有这些经历与体会。
我家那棵大楝树,长在门前晒场东南角。那时就有好心的风水先生偷偷告诉我家说,这树长得不好,离宅太近,又处巽位,早晨挡太阳,主穷。听说后也曾想挖掉,但怕被戴上封建迷信的帽子,没挖,因此,它一直长着。
大楝树是我家的标志。远来的亲戚朋友,离两三里一问,人家就回答,噢,找那家啊,门口有棵大楝树的就是。
大楝树还是一座瞭望塔。我们生产队地形比较长,东西四五华里,尽管选队长都选家住中间的人,但叫上工的号子还是听不清,谁做队长便在家门口树一面大红旗,红旗一竖便是上工,迟到扣工分;红旗一倒便是放工,再做也是白做。白做一点就当学雷锋,但迟到是不能的。我家大楝树便发挥了作用。估摸到了上工的时间,便爬上树向队长家看,一看一个准。不仅我家得利,邻居几家都得了利。但有一回,我差点挨了打。那天我从太阳偏西开始看,一会儿报告一下,直报告到大人不相信,亲自出门去看,一看太阳快要落山,急了,认为我肯定是玩忘了,没认真看。误工旷工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钱,还有很多呢!便要打我,我坚持说没玩忘。大人不信,立即向队长家跑去,回头才知道,是队长中午喝醉了酒。
晴天的时候,站在树上能望出去几里远——当然主要还是眼功好,后来书看多了,眼光就不行了,现在那怕是爬到天上,也看不清吴刚伐树了——有一回,父亲上街赶集,到了返回的时候,突然听说黑大桥断了,掉了很多人下河,不知有没有淹死的,全家人都担心起来,邻居也团过来谈论。没有办法,唯有爬上树去望。望啊望,终于望到几个人远远地走来,一步一步,终于认清了人,大家喜悦起来,邻居也散去做各自的事情。等到赶集的人回来,好像桥没断过一样,没人向历经劫难的“英雄”表示半句问候,直到吃晚饭,才又提起,才得知大桥真的断了,有几个人受了伤,有个人掉河里还没找到,父亲他们是从断桥上爬过来的。我们便庆幸,幸亏小猪没买到,要不然怎么爬回家啊?!
不过,我对楝树的情结,主要还不在这里,而在其对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守护。
那时,农村没有电灯,煤油也是凭票定量供应的,不看书不算账,家里便不点灯。邻居来我们家拉呱,能谈到我们一觉睡醒,还在谈,也不点灯。我们听多了鬼故事,亲眼看过野外鬼火(磷火)的跳跃,笃信黑的地方有鬼,天一晚便不敢进屋。虽然父亲反复对我们说,有鬼也是外面鬼多,天晚应该回家,但我们还是觉得外面亮些,便在大人回来之前始终围在大楝树周围,向回家的路上眺望,无论酷暑寒冬。印象中,生产队的工永远做不完,大人总是摸黑才能回家。大楝树发芽、开花、结枣、调零,又发芽、开花……无怨无悔,日日守护我们长大。有一回,后大河的渡船漂了,父亲上河工,母亲赶集直到不知多晚才回家,兄妹四人三个抱着树干睡着了,我担着看家的责任,不停地打盹。我想,要是没这棵大楝树,我们该倚靠在哪里啊?!
有一年防地震,我们全家在树下过了一夏一秋。一顶蚊帐,四角吊在树枝上。一张床,挤了全家六口人,人人都侧着,前心贴后背,在亲人的热量和心跳中安然入睡。太热,母亲会坐起,为我们扇风,父亲会在督查队走后,蹓进屋内睡一阵子,他不相信地震能防住,常给我们讲地震是地下鳌鱼眨眼。大楝树默默无语,枝叶间漏出点点星光,我们总是在遐想中进入梦乡。
现在常常感觉觉不好睡,可能是床太宽了,好翻身,翻过来翻过去,当然睡不着了。有时真想跟老伴说,我们试试两个人挤在一条凳子上,左右动不了,会不会像当年一样酣然入睡呢,但终究没有说,没有试。
楝树不生虫,除了短期落花外,叶子和枣子平时都不轻易掉落,在它底下纳凉、生活是比较好的。邻居家没有大楝树,防震床搭在柳树下,一天早上起来,走路一跳一跳的,又奇怪又好笑,一问才知道,是羊辣子毛飞到了床上,全家人跳了好几天。
楝树的时代结束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辛酸也已成为记忆,唯有经历过的我们,有时还会想起,心心念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