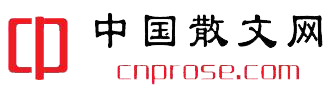我和姥姥家
姥姥家在另外一个乡镇,离我家有十几里路。姥姥家不像奶奶家,抬脚就能走着去了,去姥姥家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得提前定好时间,还得定好怎么去,多半得有人骑车送我过去。
去姥姥家的那条马路差不多是县城里最早的一条路了,我记得从县城那个老汽车站开始,往北的马路是通无棣的,正好也从奶奶家村头走。往南是通惠民的,往东再往西是通滨州,小时候滨州还叫北镇,这条路也经过我家的村口。剩下的就是往西的这条路了,姥姥家就在这条路的北边,差不多得出来县城十几里的样子。
从马路下去我记得是一条土路,开始挺宽,越往北走越窄。先要经过一个村,然后两边是大片的庄家地,再往北走就是姥姥家村里的地了,两边还有果园,我记得小舅家和姥姥家都种的有梨树。快到姥姥家村的时候,我记得还要经过一个桥,桥在姥姥家村的东边,离姥姥家的房子不远。那时候每个村的村头差不多都有一条沟渠,上面多数有个桥,沟渠大部分也是村里的劳力自己开挖的,用来引水、存水,灌溉庄家。
每次去姥姥家,差不多都是夏天放暑假的时候,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庄家,还有树上知了的叫声。路两旁的沟渠里,水是那么清澈。那时候雨水多,经常下的沟渠里的水满满的。姥姥家村头那条河里的水就挺深的,估计得有两三米。有一次我下去,想沉底试一下深度,结果憋气往上浮的时候喝了好几口水,使劲往上扒拉了好久才露出水面。
希征哥和发哥分别是大舅家、小舅家儿子,我们年龄差不多。每次去姥姥家,基本就是我们三个人玩。好几次到了姥姥家村头那个桥的时候,就看到希征哥和发哥在桥下河边抓鱼。弄一个罐头玻璃瓶子,里面灌上水,然后放点馒头,再把瓶子斜着放在岸边,一多半在水里,一部分露在外面。这样鱼可以游进瓶子里吃馒头,但想出来的时候一般都出不来了,会在瓶子里四处乱撞。不过也得手快才行,否则鱼一旦转身就能逃出瓶子了。
桥并不高,桥上经过的人,在桥下基本是能看清的。每次希征哥、发哥看到我的的时候,都会光着脚丫子边跑边喊:那不是小明吗,小明来了!
大舅的事情是我年龄大了从母亲那里知道的,每次母亲说起大舅就会掉眼泪,说大舅活着的时候又孝顺又会干活,人缘也好,深得村里人的敬重。可惜好人不长寿,大舅是在屋顶上干什么活的时候被电死了。家里撇下5个孩子,还有大妗子。如果放在现在,肯定不敢去想日子咋过下去,可是大妗子一个女人靠自己双手也把子女拉扯大了,也都成了人。想起那句话,人这一辈子,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后来想想,估计也是那时候的孩子好养活,有口吃的就行,多个人就是多副筷子的事。不像现在,都不敢生孩子了。
走过那座桥,往西一拐,应该就到了姥姥家村里那条路了,不过是土路还是沥青路我记不清了。姥姥家的房子就在他们村的东边,在村里路的北侧,大门是朝南的。记忆中姥姥家房子像一个四合院,东西南北都有屋子,从大门进去迎面是一堵墙,是东屋的那个南墙。进大门往左一拐再往前,也就是往北,就是院子了。正北面是四间还是三间土房,记不太清了。右侧也就是东边也是屋子,是做饭用的,那时候叫饭棚,我记得好像还住过人。左侧也就是西侧也是屋子,那时候记得里面养了牲口。南边我记得也是有屋子,具体干啥用的忘记了。
几间北屋就是正房了,踏过门弦子,进到外屋,靠门的右边是灶台,边上还有一个盛水的缸,记得里面经常有一条鱼。那时候玩耍回来,渴了就拿起缸盖上的瓢,舀满水咕咚咕咚喝得肚子都胀起来。有时候舀水的时候里面那条鱼还扑棱扑棱的在缸里到处乱撞。
紧挨着外屋的左侧也就是西边那间就是睡觉的屋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卧室。从外屋进去靠北墙有一张桌子,桌子靠墙一侧上面还有个长案板,上面摆着一些茶叶盒啥的。桌子对面就是一个大土炕和窗户。屋子里面西北那个墙角的地方,也就是在桌子的西侧那个墙角处,有一块离地大概一米五左右的平板,固定在墙角处,上面是一台黑白的电视机。电视机和炕中间靠墙的位置,下边是一个火炉子还有烟囱。
姥姥睡觉屋里有个神秘的地方,具体是在西侧墙上还是东侧墙上,我忘记了。那时候叫燕窝子,就是墙上掏了一个洞,外面用帘子或者挂历挡着,里面能放一些东西。每次在姥姥家住下的时候,晚上姥姥或者姥爷,就会掀开燕窝子的帘子或者挂历,伸手从里面掏出好吃的东西,有时候是花生、瓜子,有时候是饼干或者羊角蜜。总之,那个燕窝子成了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地方。每次只要看到姥姥或者姥爷向里面伸手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又有好东西吃了。
我小时候特别爱偷吃,家里有啥好吃的东西,只要被我看见,早晚我得想办法吃到肚子里。那时候农村家其实没啥特别的东西,无非就是一些水果、糕点啥,就是这些东西,在那个时代绝对也是奢侈品了。家里往往把这些东西藏在一个地方,或者锁在一个柜子里,等到走亲串门或者有客人来的时候,拿出来招待用。我当时自己住在西屋,有两个大木箱子在我住的屋里,母亲说那是她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的。有一天我突然闻到里面有一股水果的清香,但是箱子是锁着的。控制了好几天,最后实在忍不了肚子里的馋虫,晚上自己一个人把箱子慢慢搬到床上,然后把箱子转了一下,让后面朝前。找到一把螺丝刀,把箱子后面的两个合页卸掉,从后面打开了箱子,里面果然放着几个梨,金黄金黄的,放的都很软了,又香又甜,三两口就被我吃没了。完事我又把合页上好,原样把箱子放回去。后来母亲好几次都纳闷说,箱子里的梨不翼而飞了,可是锁的好好的,也没见箱子有破的地方,进不去老鼠啊。。。。
之所以写这段,是说我小时候确实馋,那么重的箱子,当时年龄小,咋就能搬动呢。现在想想,肚子里的馋虫一旦发威,力量是无穷的。可是即便自己那么馋,那么能折腾。去姥姥家那么多次,看到姥姥姥爷去燕窝子拿了那么多好吃的,我竟然能控制住自己,一次也没有去燕窝子看过,拿过。确实是没有,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想,是不是觉得不是自己家,不实着。要不就是怕被人看见,让人笑话。
岁数小的时候我去姥姥家一般都是和姥姥姥爷睡在一起,后来大了我就去外屋右侧那个屋子睡了。右侧那间屋子一进去右边也是一个土炕和窗户,和姥姥睡觉那屋差不多,靠北侧墙这边也是一张桌子。一般都是平常烧火做饭会在这屋拾掇,包括蒸个馒头包子啥的。这间屋里具体啥摆设我记不太清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有一对瓷的枕头,好像是个猫的样子,挺大,我好几次都拿来当枕头用。每次摸着都凉凉的,特别光滑,感觉和文物一样。后来姥姥姥爷去世后,这对瓷枕头也没了,据说被一个什么亲戚给拿走了。
再往东边好像还有一间小屋子,在最里面,放了一些粮食杂物啥的。
长这么大,去姥姥家好多次,也住了那么多次。与奶奶家的那种嘈杂、忙碌不同,记忆里对姥姥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安静、干净,安静是因为姥姥姥爷的性格都特别随和、慈祥,不急不躁。干净是姥姥把屋里屋外都收拾的特别干净利落,包括有时候炕上铺的褥单上有根头发,有个棍啥的,姥姥都会捡起来。另外就是,我在姥姥家不管待多久,回家的时候身上的衣服一定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姥姥只要看到我身上衣服脏了,都会让我脱下来给洗了。
姥姥脸上永远是慈祥的笑容,那种笑容让人看了浑身放松、心理愉悦。每次我去,进门喊姥姥的时候,姥姥都会疼爱的答应着,说一句:明来了蛮。
姥姥姥爷因为性格好,所以在村里人缘特别好。每次夏天去姥姥家,到了下午姥姥家过道里或者大门口有阴凉的地方,都坐满了人。大姑娘小媳妇,都拿着针线活,边干活边拉呱聊天。那时候农村特别流行一个零活,叫构花。就是人工编织一些带图案的工艺品,原料就是一些棉线。成品后可以用来铺在沙发上,或者盖在一些物品上,有的还能当衣服的配饰,比如当披肩用。那时候手工的物品很受欢迎,好多都出口了。农村里地里活忙完了,就会找一些这样的手工活来干,一是把农闲时间利用起来,二是也能挣点钱贴补家用。
晚上姥姥家的人也不断,老的、年轻的都愿意到姥姥家玩。我现在想想,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去姥姥家玩。想必还是姥姥姥爷的脾气好,去的人都会感受到一种放松和温馨,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得。每次到姥姥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放松感。不像在奶奶家,听到看到的都是那么忙碌,都是那么大声的说话,更多时候奶奶一边干活一边骂人。
姥爷应该是读过几年书,爱看报纸。记得我上大学了回去的时候,姥爷经常问我国家大事。姥爷会算卦,就是掐指算命那种。母亲和我说过好几次,说她大概知道姥爷算卦的路数,比如最后要是落到了“大安”上,可能就比较好。听人说,有好几次村里人丢了东西让姥爷算,姥爷确实是给算出来了,包括丢东西的方位,大概几天能找到。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也想不清楚。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奇妙,我猜想可能是姥爷掐指一算的那一刻,姥爷开了天眼,与丢的东西产生了感应,然后他就算出来了。
有一次姥姥把一只鸡扣在了盆子里,说鸡丢了让姥爷给算算。姥爷算了半天说够呛能找到了,结果姥姥一掀盆子鸡从里面跑出来了。
姥爷有个烟斗,抽了好多年。后来改抽旱烟,就是自己用纸卷烟叶,烟叶放在桌子上那个案板上,一个铁盒子,外面都被摸的发黑了。每次姥爷用手捏一小挫,放在已经撕好的一片方块纸上,然后往两边捻一捻,再从一个角慢慢卷起来,最后用舌头舔一下纸的另一个角,粘在烟卷上。烟卷一头再用手使劲捻一捻,防止烟叶掉出来,另一头含在嘴里,就可以把捻的那一头用火点着抽了。
我几乎没听到姥姥和姥爷吵过架,虽然去姥姥家次数比去奶奶家次数少,但记忆里还是愿意去姥姥家,去了也愿意住下。不只是有好东西吃,还有希征哥、发哥陪着玩,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浓浓的温暖。除了脾气性格上的差异,也许还是各自的家境不一样吧。听母亲说姥姥家以前是地主富农,家里条件还是可以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姥爷还受到过批斗。村里有一个当时参与批斗姥爷的,好多年过去后,我问姥爷恨不恨那个人,姥爷说不恨,恨人家干啥呀,那时候都那样,家里亲爹亲儿还有出人命的。姥爷看事很通透,心里没有怨恨,这是我最佩服的地方。
我每次住姥姥家的时候,早上姥爷起的很早,出去拾粪。那时候农村里还没有什么拖拉机等机械设备,各家都喂牲口,下地干活牲口能出不少的力。牲口多了,就会满地排泄大便,不管是牛还是马,还有骡子。经常是村里的路上、田间地头都是牲口留下的粪便。姥爷早上早早出去就是去拾这些粪便,挎一个有着长长把的粪筐,手里再拿一个拾粪的钩子或者锄头。拾回来的粪便一般都会倒在自己家的猪圈里,当成肥料定期的上到地里。
差不多应该是从我上高中的时候开始,过年去姥姥家,一般都是初二去,给姥姥姥爷磕完头拜完年,中午一般都会到村西边小舅家吃饭。小舅一共9个外甥,每次都是等人到齐了才开席,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年年如此。小舅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厕所都拿着报纸,我现在想想,我语文好都是在厕所里看报纸看的。小舅从四五十岁的壮年也到了现在七八十岁,每年和小妗子还是给我们张罗端菜,陪我们喝酒。姥爷活着的时候,每次到了中午小舅家饭菜上齐之后,都会接姥爷过来,有时是姥爷自己骑三轮车自己过来。陪着我们喝一杯酒,说说话,姥爷慈祥的会看看每一个人,每次都是不吃饭就回他东头的房子里去了。如今发哥都都当爷爷了,一辈辈的人就这样新老更替,转眼间我们都已经四五十了。
华姐是姥姥家一个“特殊”的人物,之所以说特殊,一是华姐待在姥姥家时间很长,二是华姐出嫁的时候是从姥姥家村里出嫁的。华姐是大姨家的孩子,大姨家一共有5个孩子,那时候孩子多、日子难,华姐从小就跟了姥姥,我不记得华姐是从多么大去的。反正从我记事起,每次去姥姥家就会看到华姐,记忆里华姐一直在构花,不停的构,话也不多,对我很好。不过,华姐在姥姥家的日子里,确实给姥姥家干了不少活,就当是姥姥养了一个闺女了。华姐因为待的时间长,和姥姥村里的人很熟很熟了,成了村里真正的一员。华姐是从姥姥家出嫁的,据说那天华姐、姥姥姥爷都流了不少泪。人世间的儿女固然有生之恩,更多的也是养之情,和姥姥姥爷生活了那么多年,我觉得华姐一定也是把姥姥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本就是亲人的姥姥姥姥爷当成了更亲更近的人。出嫁之后华姐每年和姐夫也都回老家看望姥姥姥爷,中间都是那份难舍难忘的亲情。
姥姥去世的时候我没在家,说是在小姨怀里闭上的眼睛。姥姥走之前,没得过病,没吃过药,就那样安安静静的走了,就像我每次去姥姥家那种感受一样。姥姥活着的时候没有麻烦过别人,走的时候也是那样干净、安静,没有给儿女添一丝一毫的麻烦。这种安静,让我们都感到那么不忍、不舍。我常常想,姥姥走之前都没舍得咳嗽一声,感个冒发个烧,前一分钟还在和你说话,后一分钟就闭上了眼睛,走的那么慈祥和幸福。
姥姥走后姥爷的精神明显不如以前了,尽管我们这些小辈们也断不了去看望他,但终究比不过姥姥活着的时候两人的相互照顾。姥爷88岁那年我回家过一次,当时还住在老家的那个老院子里,因为老院子是土墙,夏天更凉快一些。当时姥爷已经不能动了,几个子女轮着照护。冬天接到新盖的房子里,姥爷意识不太清醒了,大小便也没法自理,手不受控制的到处乱抓,尤其是大便后如果不注意他会抓的到处都是。有一次母亲说她外出几分钟去村里小卖部买了点东西,回来一看姥爷把大便抓的满屋子都是,包括墙上,因为是刚盖的房子,墙都是白色的。母亲说她当时很焦怨,一边收拾一边流着眼泪和姥爷说,俺这都是新盖的屋,你咋这么能作践人啊。。。。。
人老了,谁能想到会是什么样子呢?每次母亲和我说的时候,我都在心里想,等我们老了,也会和姥爷一样吗?也许还不如姥爷呢。我和母亲说,兴许是姥姥走的太安静了,没有让你们子女使一点点心。姥爷老了,多少让你们操点心,等将来姥爷走的时候你们也会安心一些。会觉得当儿女的还是照顾了一下自己的父母,尽管这种照顾与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比起来,那么的微不足道。
姥姥慈祥,姥爷正直。童年在姥姥家的成长经历,也对我的性格有很大影响。从小念书还算用功的我,经常被姥爷说,能给共产党当好官。长大了没当上什么官,不过无论到那里,无论干什么,总是勤勤恳恳,本本分分。
姥姥家那个村还在,除了姥姥姥爷。姥姥家的房子没有了,村里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小时候的庄稼地、村口的小桥、桥下的流水,还有那一片片的果园,好多都没了。每年去小舅家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不像小时候骑自行车感觉要走好久,路上能看到很多风景。尤其是当离姥姥家村口越来越近的时候,那种激动兴奋的心情现在似乎没有了。
脑海里总会想起一个场景,姥姥站在大门口,向东边张望着。大都是看我和发哥、希征哥在外面玩回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