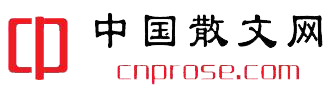《天涯》2024年第2期|江映烛:音图
江映烛,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无杭》《脊轩》等。
音图
江映烛
“(温峤)旋于武昌,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燃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怪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峤其夜梦人谓己曰:“与君幽明道别,何意相照也?”
——《晋书·列传第三十七》
一
我三十岁那年,发生一件事情,让我对这个世界的本质产生了怀疑。
那时,我被困在现实世界,一事无成。于是在一个备受煎熬的年末,我卷了一床铺盖,上了一座山,进了一座几无香火的草木寺,去写一个无人在意的故事。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在我进寺三个月后。农历三月初三凌晨,我从书桌前惊醒,发现电脑屏幕依旧亮着,光标闪动。我揉揉惺忪的睡眼,凝目看了一下时间,凌晨四点二十五。
正当我要保存文档上床睡觉时,屏幕上弹出“电量不足”的提醒,这让我察觉出某种异常。睡着之前,我没有给笔记本电脑插电,因为这间禅房里唯一的插孔贴近床脚位置,我的电源线不够长,我都是白天充好电,晚上写。我的笔记本电脑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十分钟就会自动进入睡眠状态,而我显然睡了不止十分钟。
我抱起笔记本电脑走到墙脚,插上电翻看文档,一看之下,悚然心惊。不知什么时候,我竟然把故事里灵书素、孤直公、谢臻、萧玄翼这四个人物,都给写死了。
灵书素死在一个草长莺飞的午后,被一只叫猫小僧的小猫带着爬上洛阳城的城楼,随即纵身一跃,飞入云海中。
孤直公忽然逸兴遄飞,在半夜溜入皇宫,坐在皇帝爱妃的屋顶乱弹几曲,琴声呕哑嘲哳实在难听,被巡夜的护卫以“扰人视听罪”就地正法。
谢臻把商陆当成人参吃了一整根,由此安静上了路。据说神农氏尝百草,吃的最后一样东西,就是这个玩意儿。
萧玄翼就更加离谱,他趁着日出奔出洛阳,舍弃了坐骑一路向北,逢山跨岭,遇水横渡,几乎沿着一条笔直的线路奔至古时的北海——如今的贝加尔湖,从湖的正南部入水,游至一半,冻毙在无边无垠的湖水里……
我深感难以置信,这些诡异的桥段,是出自我的手。这样的情节,毫无道理可言……
我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在天人交会的地方,我下笔有了灵感。孤灯将我悬起来,像在写野草集。
在万物归冥之际,我感到一种深远的寂静。每当我悬笔,睡过去,再醒来,故事的走向就变得匪夷所思。
书里的人逃了出来,我拿了一张罗网,却没全部抓住他们。
二
从那一天开始,各种奇怪的事纷至沓来。
我总是在每个神思杳杳的孤夜没来由地昏睡过去,醒来后,我笔下故事的走向就会自动更改,但我想不起来自己何时入眠,何时写下这些文字。
起初,我安慰自己这是神来之笔,后来发现不对,我得搞清楚这个事。
我央求草木寺的小和尚玄见带我下山,去最近的县城,置办一些东西。
玄见和尚比我小十二岁,是个有些木讷但精力充沛的小僧,我平日里喜欢逗他,所以交情不错。他没事时会跑来我的禅房看我写的东西,更喜欢借我的电脑看一些老电视剧,什么《天下粮仓》《宰相刘罗锅》、87版《红楼梦》都是他的挚爱。我说他凡心未泯是个假和尚,他说阿弥陀佛不能瞎说。于是我把他也写进了我的故事里,改名为玄剑,成了一名杀人不眨眼的杀手,他嫌戾气太重,我又改作玄翦,变身为一位千里不留行的刺客,他表示很满意。
与我交情不错的,还有一只名为猫小僧的寺猫,我还没来得及将它写进书里,第一次见到关于它在书里的描述,就是在三月初三的那个凌晨,它将灵书素带上了洛阳的城楼。
玄见带我去了最近的县城,我请他吃了碗素面,然后找理由支开他,让他等我,我去办事。
再上草木寺,我的包中多了几本书和一个黑袋子,袋子里藏着一个公牛插线板和一个可以连接手机的小摄像头。
当晚,我悄悄将摄像头安装在房间里。隔天,我就在监控中看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
约莫凌晨两点,正在写作的我毫无征兆地睡着在座位上,半个时辰后,原本睡着的我忽然坐了起来,将熄灭的屏幕重新点亮,眉目紧蹙,按了半晌退格键后,开始打字。
我着实吓了一跳,想起电影《闪灵》里男主杰克·托伦斯精神失常后在打字机上反复敲打一行字的情节,心脏都停搏了几秒。但我并不热衷于灵异与离奇,我上山来,不是为了给自己本已庸常的生活再增一分难以解释的诡秘。
同理,我更不会把这件事嚷嚷出去,让自己受到关于神志方面的质疑,进而与精神病院扯上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我的人生会更荒蛮一成。
我很快镇定下来,欲将此事抛诸脑后。我决定暂时不用电脑写作了,改成纸笔,一来是梦游状态下的自己按着退格键删除清醒时写下的既成文本太过容易(这一点甚至比看到自己梦游乱写还令我害怕),二来是电子产品总令人目眩神摇,或许,就是这样。
三
我上山两个月后,老和尚空闻曾专程跑来问过我上草木寺的原因,我含含混混回答过,说的都是真话,但没说全。
我上山的原因,跟我笔下的萧玄翼很像,萧玄翼是个“持志若心痛”的人,而我则有一种“持志若心悸”的感觉。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老和尚空闻,老和尚派小和尚玄见隔天下山,给我买了瓶速效救心丸,让我尽量别死在山上。
那段时间,我是那样的逡巡、犹豫、徘徊、踟蹰,我知道它们大致表达的是一个意思。
每当太阳渐渐下去,空虚就从另一个世界荡过来,盘踞在这个世界的方寸之间,其间莺飞草长、桅杆数点,都已与我无关。某种力量正在剥夺一个叫“豪迈”的词,与之相关的铁马秋风、壮声英概,都随之而去。
我难以入眠,成宿成宿地难以入眠,细想着生而为人的各种细枝末节,关于热情,关于匮乏感……
我在草木寺想人生那点事的时候,孤直公也在我书里想人生那点事。他是个三十多岁仍然一事无成的书中人,多少有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一点跟我有点相似,而他想不明白,我也想不明白,这点又和我相似。
如今又添了这档子梦游乱书的事,我变得比孤直公更加困惑。
梦游乱书的事我没有声张,也不敢声张,只是在私底下折磨了我很长时间。我养成了看监控的习惯,我会仔细观察自己在无意识状态下的一举一动,和那些失常却连贯的梦中文字。
我坚信自己的精神没有问题,无论是我的行为模式、逻辑思维能力还是与人的交际,都跟昔日大抵相当。但我还是想搞清楚一件事,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我不断更改故事的走向。
在改用纸笔写作后,进度相较之前更加缓慢了。好在,纵然再有类似神游写作的事情发生,我的手书速度也有限。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手写时,虽然我屡屡在人物命运方面胡言乱语,却没有手撕前稿的习惯。
我只需在清醒之后,将睡着后写的稿子弃置,续上清醒时写的前作即可。
笔记本电脑被我暂时寄放在了玄见小和尚那里,我锁了原先的那些文档,防止咄咄怪事的发生。
监控里,孤灯将我悬起来,我抽出纸笔,像是在写野草集。
在万物归冥之际,我感到一种深远的寂静……
四
在草木寺,老和尚空闻之于我,有点像马尔克斯的姥姥之于马尔克斯。
他念的经我自然都听不懂,但就是能让我有所启迪。这种启迪不在经文本身的含义,而在于个人的感受,我感觉他念诵出口的,是一种古老的秩序。古老的秩序传续有度,本就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
我轻易地从繁杂的声浪中辨析出这种古老的音质,他的腔调不紧不慢,在不知所云的念诵中时时谱写旋律,雾霭、湖泊、宏大、细微,抛离了意识、形态与镣铐。
往往听到一半,我就会见了周公,比安眠药都管用。
小和尚玄见说我没有慧根,空闻却从来不这么说,他只是在我醒后提醒我,只要捐了香火(伙食费和禅房的住宿费),其他的事都好说。
我被神游的事折磨得不可开交时,就经常去听他念经。
听经,我会选择一个舒服的姿势,把猫小僧横放在腿弯,摸着它肉乎乎的头。它是一只受过戒律的猫,横在腿上像抱着一把古琴。我不将其视为寻常猫,而空闻却没觉得它有什么不寻常。他说这叫分别心,放下分别心,才能观自在。
我说,师父你没有分别心,所以没法写故事,只能说境界。你不懂写作,我不懂禅。
我在被空闻的诵经声催眠了几十次后,忽然有一天,我察觉到了自己梦游写作的根节。我压根不是自己睡着的,而是被书里的人催眠了。
我懒得对书里的人稍加控制,我想看看他们究竟要做些什么。
接着,在我不动神色的纵容下,他们的命途越来越离奇。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自己再次将萧玄翼写死,我开始意识到,或许,他们只是想逃离。
我坐在白与黑的间隙,看日头寸寸下移,怀疑着人间的真实性。
五
书里的故事发生在公元一千三百年的一处大泽边,主人公萧玄翼有一个念头,想要带灵书素一起看海,于是他在一处大泽边遇到了灵书素。
灵书素是个画师,披着一席三丈长的大氅,她想画下整个洛阳,画完了洛阳就准备西进长安,进而画出八百里秦川、九万里风月。但她作画不用笔,每当她睡着,梦里的场景就会拓印在她神奇的大氅上。
在书里,萧玄翼并非本来就要带灵书素看海,他是个万里奔丧的孝子,立在一叶孤舟之上,要北上到一片连大海都结冰的地方,去见一个人。直到他在大泽边遇到了灵书素,命运的纺线改变了轨迹。
二人的行动路线并不相同,一个向西,一个往北。但上天(也就是我)让他们遇见,一道走了一程,到了洛阳我为他们描绘了一个繁华的都市,满城弥漫着花香。
在这里,他们认识了一些奇怪又生动的人,比如孤直公、金楼子、谢臻、谷音、垂髫。
孤直公是天下第一琴师,擅长弹琴,他的琴声裂云穿石,能唤明月。
金楼子是天下第一书生,善于长啸,有一副“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徵”的好嗓子。
谢臻是个厌恶木屐的闺秀,经常偷偷地赤脚走在阁楼和林荫里,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让她与那些矜夸服饰以为显赫的木偶人截然不同。
谷音想要熔掉自己的命运,借助一把锻造神剑的火,她要在洛阳城内外寻找一个能生出天下最纯粹火焰的火炉。
垂髫则是一个携个竹篮疯跑在阡陌之上的小孩,篮子里盛满了他在地头捡到的麦穗。我叫不出他的名字,就根据他的年龄随意为他取个名字,叫垂髫。
至于为什么要疯跑,是我觉得,疯跑起来会有乘奔御风的感觉,他会感觉到快乐。于是他有了个梦想,长大继承神行太保戴宗的衣钵。至于为什么能盛满了麦穗,是我想营造出一种五谷丰登的错觉,纵然天下的大背景是饥荒。
跑起来的人,好像能摆脱沉重的疑窦,有疑窦的人,都不会这么疯跑。
或许,他在我书里跑过的里程,已经远远超过了古希腊的斐里庇得斯——那个为了传递战胜的喜讯跑到雅典过劳而亡的士兵,人们为了纪念他设立了马拉松项目……
然而在近期的故事里,他们的动线全变了,抛开视死如归的灵书素和萧玄翼。
孤直公用他当世无匹的琴技,反复演奏出中人欲呕的噪音,在每个深夜持之以恒地吵醒睡得正熟的萧玄翼,惹得萧玄翼屡动杀念。这里的“中人欲呕”并非一个形容词,而是能让人真实产生生理反应的噪音,萧玄翼甚至能在睡梦中因为听到孤直公弹琴而吐出来呛到自己。而他俩,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甚至还是患难与共的知音与挚友。
金楼子的嗓子突然倒了,不是戏曲名角的倒仓,更像是刺客豫让那种漆身吞炭导致的嘶哑,一张口神厌鬼弃。
谢臻开始锲而不舍地拿商陆当饭吃,毒性尚未发作的短暂间隙,她会像幻影一样飘离卧房,赤脚在夜里跨越家中三进院子的高墙,义无反顾往外闯,或扑倒在墙下,或昏死在道上。
谷音终于在洛阳城里寻到了那个能生出天下最纯粹火焰的火炉,但等找到后,却剪去头发,洗净身体,将自己投诸炉中,像在效法干将莫邪锻剑的故事。
垂髫则总想跟一头脾气暴躁的野牛抵头,他一个小屁孩,穿个红色的肚兜,每次跑到野牛附近,都会发出一声挑衅的呼哨,风也似的埋头奔过去……
显然,他们是想尽早为自己找个并不体面的归宿,结束其在书中的一生。我难以理解,毫无头绪。
我给书里的人打造了一个美丽的伊甸园,却不知道他们为何想要逃离那里。
随后的日子里,我将自己闷在房子里看书,不愿再动笔,直到头发长得跟灵书素一样长,小和尚玄见叩响了我的房门。
六
玄见带着猫小僧拉我出门,说是要给整个草木寺大扫除。从院子到大殿,角角落落。
我说,我供了香火,难道不能免于劳作?老和尚空闻从一个回廊转出来说,不能!
我问,为什么?空闻说,所谓大扫除,包括你在内,都得扫除。
我被逼迫去洗了个不冷不热的澡,换了身干净衣服,空闻要给我亲自操刀修剪发须,在此过程中我反复强调我没有出家的打算,但他拿手的发型似乎只有光头。
我在落发成为光头的几分钟内,空闻给我讲了个故事。他说,你如果想做一件事啊,要真正想做才行,真正想做的时候,外面的声音就会变小。就像玄奘法师西行求法,不是唐太宗派去的,而是以通缉犯的身份偷渡到西域的。那时候大唐与东突厥战事正紧,唐廷严令禁边,玄奘自己要践行西行求法的宏愿,于是乔装打扮,从长安到了瓜州,又从瓜州绕过了玉门关。在此期间,一个叫石磐陀的胡商,也就是小说里孙悟空的原型,只跟了师父一小段路,其后八百里大漠、五万里疆土,都是玄奘一个人走下来的,一走就是十九年。等他回来时候,唐朝已经肃清了边务,一个崭新的大唐敞开国门等着他。
我说,师父我懂了,你是想让我当逃犯。空闻说,低头吧。我低下头,他舀了一瓢冷水,浇在我头顶,勺底落在我后脑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我陪玄见扫了两天院子,干完一应杂事。第三天正午,他揣了几个烤好的土豆,邀我去爬后山,日头正好,我欣然同意。后山的悬壁上有个洞窟,洞窟左近有数个佛窟环绕,我一直觉得那里有故事。
猫小僧在前开路,我们随着它盘山而上。沿途弯弯绕绕,尽是些寻常山景。
玄见说大扫除和拉我去山上转,都是空闻师父的意思,老和尚看出我精神上的不安宁,记得我有心悸的毛病,怕我长期窝着突发心脏病死在山上。
我将玄见塞给我的速效救心丸装进兜里,表情僵硬勉强谢过。
后山看着不远,走起来实在不近。我们过了一处山涧,再往上走,走了一半,太阳已悬不住了。玄见望了一眼天光,住脚拿出土豆,说吃完土豆我们就该折返了,但我还惦记着洞窟,问能不能再走一段。
于是我们吃着土豆加快了脚步,但终于还是没能抵达。
我在山道上捡到盏煤油灯,捻子和灯油俱全。
我提溜起来问玄见,这像什么?他说,像林黛玉给贾宝玉的玻璃绣球灯。
我哈哈大笑,说他长大肯定是个花和尚,他说阿弥陀佛,不要瞎说。
悬壁上的洞窟还有很长一段栈道,我们在走了一段后预估了时间,到那里恐怕就赶不及天黑前回寺了。玄见面露难色,我又不可能独往,加之猫小僧也走乏了,跳上玄见的肩埋头就睡,爪子将他的僧袍都勾出线来了,于是我们决定原路折返。
回来的路上,我们在一棵巨木的背阴处发现一处水潭,这时余晖未敛,从树荫投射出一片朦胧的雾,笼罩着深不见底的泉水。
我点燃煤油灯照潭水,水中影影绰绰,难辨水中事物。旋即雾的罗帐垂下来,我隔着帐子见到潭中有一杆画戟,万物追逐,有人跌跌撞撞奔跑在丹墀之上……
玄见忽然横臂过来,压下我的胳膊说,不要照。
我回过神来,一阵山风从枯槁的林间荡过来,我的脑袋感到分外寒冷。
我们回到草木寺时天已黑透了,玄见和我道别后就回了自己的禅房,我进屋想思考些什么问题,但一沾枕头就睡得不省人事。
第二天我从梦里醒来,玄见小和尚说他没见过什么潭水。
我看看立在墙脚的煤油灯,心里知道,那是一方迷误的世界,藏匿在一片迷雾之后。
七
我决定善用这个“玻璃绣球灯”,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我捡到它,它就该有它的用处。
于是我开始在深夜点灯看书,一点就是一夜,但这灯破了一个口,散溢的烟气每天都熏得我眼睛很迷。我也不是非要看书不可,而是必须用看书这个事情,填补令人心悸的负罪感。
玄见来找过我两次。第一次问我近期是不是在练什么透支身体的功法,要成火眼金睛,恐怕得进炼丹炉。
第二次是来为空闻师父传话,嘱咐我半夜别点火,我莫名其妙,我说我没点火,我点的是煤油灯。我引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的诗句对他说:“啊!灯光下的世界显得多么伟大!/而在回忆的眼中,世界又何其区区!”
玄见私下问我有没有烧庙的打算,我正色说这是哪里话,我好歹是个文化人,能做放火烧庙的歹事?
三天之后,玄见又持着空闻师父的字条来,说是最后通牒,上面写着:“昼坐惜阴,夜坐熄灯。”
我看后哈哈一笑,取笔在字条上纠正,将“熄灯”改成了“惜灯”,对玄见说:“拿给师父看,是熄灯吗?错了,是惜灯,这里的惜,是珍惜的意思,一字之别,差之千里。”
玄见将我批改的字条拿给空闻看,空闻嘱咐玄见,让他安排一下我的下山事宜。
我让玄见别开玩笑,又捐了点香火,后几晚早早熄灯,这才作罢。
但纵然熄了灯,我的作息却一时调整不过来,就像习惯了夜行的雕枭。
于是我整宿整宿地躺在床上,躺不住了,会起来,裹着被子坐在桌前,看窗外。
黑暗中,我看到了很多东西,万物一张一翕。有时候,我会掂量自己在这人世上的重量,甚至偶尔会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很重要。这种谵妄的幻想不无作用,因为幻想会让我产生别人认为假而我在那一刻认为是真的虚假满足感。
我想真正相信“心外无物”思想的人,会不会比钢铁般百毒不侵的唯物主义者稍微快乐一点,他们每天在心里念叨着“离却我的灵敏,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这样,他们只需要寻找自己的灵明。当然,这只是我众多妄想中的一个,跟佛家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不相干,跟我这个人平时的行事准则也不大相干,更没有要否定唯物论的意思。
我想把自己发散的灵明都抓捕到纸面上,可我不想动,抽纸的空隙,那些活蹦乱跳的、忽左忽右的、踩着风火轮和筋斗云的乱念,会一去千里。
我想写它们,又不想写它们,因为还不够华彩。
我打开稿纸,月光下,我竟然也能看清纸张上的每一个人,灵书素、萧玄翼、金楼子、谢臻、孤直公、谷音、垂髫、玄翦……他们变换着身姿,活在虚无之巢、恍惚之场,是我将他们扯进这个奇诡的世间,来抵御我个人的失落与困顿。
八
我开始在半夜听到琴声,伴随大声朗读诗书的声音。我知道他们是谁。
孤直公对着月亮抚弄着他那把破琴,为读书的金楼子配乐。
他们一个盘坐、一个游走在我的禅房屋顶上,踩得瓦片咯吱作响,金楼子的破锣嗓子穿云透雾,恨不能声震寰宇。
孤直公在我书里因为乱弹琴已经被正法了很多次,可是善长啸的金楼子性格清冷,是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稳重人,我没想到他竟然也能被策反。
我这头自然没有大碍,但草木寺里还有小僧玄见、老僧空闻以及壮年僧人广智、广元四人常驻,当然还有只猫小僧。我没法向他们解释这件事,他们认定了是我半夜发神经,要扰乱净土的清净。我只好摊手说人生就是会吵吵闹闹,在某些莫名其妙的时刻。
有天夜里,孤直公叫上金楼子再次奏乐,却一反常态地认真起来——《秦王破阵乐》,我闭上眼睛,眼前浮现灵书素排众而出的破阵舞。这是贞观七年李世民加以完善的舞蹈:“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灵书素身披大氅,往来驰走,配合着孤直公的琴、金楼子的鼓,每一步,都踩在乐律的刀尖上,激昂踊跃,仿佛已刺破生活的沉闷,焕发了新生。
我心想来了,不服管的家伙们,终于步入了正轨……然而好景不长,正当我沉醉之际,乐声陡变。这时我才发现,灵书素率领的舞众——那群看不清相貌的书中舞姬,早已变换了阵型,以一种匪夷所思的合围之势,将我困在中央。我恍然大悟,不是《秦王破阵乐》,是《秦王陷阵乐》!压力山呼海啸,滚滚而至。
我惊叫着醒来,连人带被子被抬下了床,抬我的广智和广元冲我粲然一笑,玄见正将我枕头底下压的书收入纸箱中,外面天光大亮。
我无处借力,勉强抬起头疑惑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玄见晃了晃手里的书说,杯酒释兵权。说罢把书扔进纸箱,转身抱着纸箱往门外走。
我说,听听,听听!你都说什么话,什么叫杯酒?这是你们佛门中人能说的?什么叫兵权,书能是我的兵权?
广智和广元将我扔回床上,又拿起枕头抖了抖,确保枕头里没书。
我大叫着说,拜托别这么离谱,私闯民宅,要负法律责任。
玄见不等我说完就从门外进来封了我的口,他再次传达了空闻方丈“口谕”,让我最近别再看书,多上山看看树!
我想起陆游有首诗叫《高秋亭》,我记得其中两句“从今惜取观书眼,长看天西万叠青”。我问方丈是不是这个意思,玄见问后说是。
我又问玄见,师父为什么不亲自来跟我说?
玄见说,师父怕见到你,忍不住破了嗔戒。
……
(全文请阅读《天涯》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