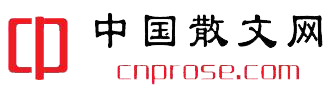《四川文学》2024年第3期 | 周齐林:风叩门环
1
一阵风吹来,门环发出清脆的响声,声音回荡在记忆的深井里。
门和窗是房子的眼睛,温暖的阳光透过它们涌入屋内。门是隐私的屏障,关闭门和窗,便暂时隐匿在属于自己的城堡里,可进可退。阁楼上,年幼的我手持一台半旧的军用望远镜,透过窄小的窗子观察着屋外的一举一动。
晨曦时分,母亲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开门。沉重的木门被推开,发出嘎吱的响声,沉睡的村庄也跟着醒过来。紧接着,村里一扇扇紧闭的大门慢慢敞开,阳光瞬间吞没黑暗。一直到深夜,一扇扇门才关上。
村庄是一个巨大的连通器,这里鸡犬相闻,耳鬓厮磨,牵一发而动全身。薄暮时分,凉风习习,村里人都端着饭碗聚集在村口的空地上,一边吃一边唠着家常,分享着各自碗里的菜肴。夜的幕布完全落下,如水的月光洒落在大地上,恍若白昼。夜半躺在床上,夜风吹拂门环发出的阵阵响声不时传入耳中,伴我入眠。母亲的一声咳嗽回荡在夜空中,传递到每个村里人的耳里,在他们心底泛起阵阵涟漪。
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一道道门串联在一起,紧密相连,编织成一个村庄的模样。
秋收过后,时光的脚步仿佛停滞下来,此刻的村庄是安静深沉的。经过夏秋两个季节忙碌的收获,村里的人终于闲了下来。村里人三五成群聚集在屋里纳鞋帮,屋外的空气已有了些微寒意,大门紧闭。寒风透过窗棂的缝隙吹进屋内。屋内点着炉火,温暖如春。老头儿双手伸进袖管里,缓缓往茶馆走去。只有孩子们还要背着书包去上学。调皮的孩子看着家里人都闲在家里,嘟噜了一句,惹来满屋子的笑声。
五额婶是蓝塘村人,与我的外婆同村。因了这层关系,母亲和五额婶走得很近。母亲常去五额婶家串门,有时会带去蔬菜,有时会带一些糖果。五额婶就住在我家对面,相隔不到五十米。五额婶比我母亲大二十岁。母亲生我那年,寒冷的冬天,呼啸的寒风如一把把冰冷的刀,还没出月子的她挽起裤脚去湿淋淋的稻田把浸泡多日的油菜拉上岸,自此就染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几十年下来,天气稍有变化,母亲的腿就隐隐地疼。
随着时间的推移,疼痛变得明目张胆。母亲疼得满头虚汗,面色苍白。疼痛来袭时,母亲端着一瓶活络油,拿着刮痧的白勺子,推开五额婶家沉重的木门,让她帮忙刮痧。母亲弯腰坐在板凳上,五额婶拿着白色的瓷勺子,沾点水,水起润滑作用,刮起来得力,不会伤及皮肤。五额婶由上而下娴熟地刮起来,在母亲的背上刮出一道道细长的痧痕。刮完痧,五额婶在我母亲的背上涂抹一层活络油,母亲顿感全身轻松许多,仿佛身上的湿气被拧干了一般。
那个午后,五额婶捂着胸口缓缓瘫倒在地。恰巧这时,我母亲端着活络油,拿着刮痧的白勺子走进门,她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五额婶心脏病发作,母亲急忙进屋取来药给她服上才幸免于难。
多年后,这个场景一直盘踞在我的脑海里。在时间的发酵下,它成为一种隐喻,不停地敲击着我的胸膛。
2
时光流逝,当年在午后的风里奔跑嬉戏追逐的我已远离故乡,来到城市。
城市里的门五花八门。工厂密集的南方小镇弥漫着铁的气息,每个厂门口都守卫森严。
2007年,刚大学毕业的我进了东莞寮步镇一家一万多人的台资厂。厂规严格,每个员工须佩戴厂牌进出。未佩戴的每抓到一次罚款一百元。彼时,月薪只有一千八。厂牌分黄、蓝、黑三种。普工员工佩戴黄色,中层干部佩戴蓝色,总裁办的佩戴黑色。我本应该佩戴蓝牌,后因在总裁办负责外贸工作,人事部给我发了一张黑牌。厂牌是身份的象征。当我佩戴着厂牌从厂门口经过时,我看见门口的保安长久地盯着我脖子上悬挂着的厂牌,眼底满是惊讶和羡慕。
早上,临近上班时,我常看见在外租住的工友因厂牌落在出租屋里而被保安拒之门外。一个年轻的女孩因没带厂牌蹲在厂门口哭泣。任她如何求情,保安都置若罔闻。一次我因在外留宿,厂牌遗失在酒店里。眼见上班时间临近,焦急的我故作轻松地往里走,走至厂门口的瞬间,保安忽然厉声把我叫住。“我是总裁办的,刚出差回来,厂牌落在家里了。不信你打电话问问?”我忐忑地说道。保安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一眼,最终把我放了进去。
在偌大的办公室,总经理的办公室比较特别,安装了单向透视玻璃,站在外面看不到里面,里面却能把外面看得一清二楚。在大办公室上班的人,每分每秒都正襟危坐,我时刻做出冲锋陷阵十分忙碌的模样。在一双双无形的眼睛的监视下,办公室形同牢笼。彼时的我初入社会,每隔一个小时总会借故看样品跑到下面的车间透气放风。
门内的世界深不可测,欲望在这里沉浮蒸腾。一天深夜,我看见业务部的主管走进了总经理的办公室,半个多小时出来时,她头发略显凌乱,面色绯红。一扇门把我隔离在外,我隐约能想象到里面发生了什么。一周后,在众人的惊讶声中,她成了业务部的经理。
宿舍是四人间,门是铁门,一个窄小的窗户安装在靠近走廊这边。下班后,大门敞开,屋内烟雾弥漫。我们时常为是否开门而争吵不休。睡在我上铺的阿勇想关门安静看书,一旁的阿华却坚持打开门通风。他们争吵得面红耳赤,差点动起手来。这扇门和窗不属于我。在工厂宿舍住了一月有余,渴望一扇属于自己的门和窗的想法愈加强烈。发工资后,我终于在外面租住了一个月三百的房子。一室一厅,很宽敞。门是防盗门。窗很大,窗外是一条哗哗流淌的河流,河流两岸一排排高大的榕树,枝繁叶茂。深夜,周遭安静下来,静静地躺在床上,能听到哗哗的水流声。晨曦微露时,树上的鸟鸣声不时传到耳边。河流、树和鸟的存在让弥漫着铁的气息的工业区多了一抹诗意。
我在台资厂做了不到半年就离职了。许多年后,当我带着怀旧的伤感,驱车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停车的刹那,打开车窗,我看见厂门此刻已锈迹斑斑。朝里张望,厂房空荡荡的。
离开台资厂,随后的这些年,我辗转颠簸,东莞寮步、虎门、道滘、万江、厚街,深圳上沙、广州白云区,这些地方都留下我的气息和足迹。一道门随着我的离开而关闭,另一道门随着我的离开而敞开。我在气息不同性格迥异的门之间穿梭徘徊,直至筋疲力尽。
深夜,火车发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它庞大的钢铁身躯映衬着我的虚弱与单薄。2011年,大病初愈的我拖着虚弱的身体重新回到了东莞。几经辗转,我在寮步一家模切机公司做文案策划,试用期三个月。厂里的办公室都是透明的玻璃门,上班的铃声响起,每个人都正襟危坐,一脸严肃。工作一月有余,一日快下班时,主管忽然跟我说,转正的名额只有一个,到时从你们两人间选一个。另一个是主管的远方亲戚,半个月前招进来的。主管还想说什么,我忽然起身,用力甩开凳子,走出了门。次日下午,我结完工资离开了工厂。站在厂门口,望着车流密集的马路,我忽然不知何去何从。疾驰的汽车都有自己的方向和目的地,它们车门紧闭,车窗偶尔露出一条缝隙。我像一辆抛锚在半路的汽车,进退两难。
几天后,我孤注一掷,租住在寮步消防支队附近的一间出租屋里,做自由撰稿人。
白天,我伏在电脑前,逼迫着自己批量生产着各式文字。足不出户,生活简单到只剩下一台电脑。好友峰在一里外的一家制衣厂上班,峰晚上不加班时,会过来看我,陪我聊天。峰见我整天在外面吃快餐,有个晚上,给我送来一个六成新的电饭煲、两个吃饭的小碗以及两个装汤盛菜的大碗。我从超市买来了米和红枣,早上起床煮粥吃。吃完早餐,在键盘上敲一两个小时,到附近的菜市场买一点肉和排骨炖汤。
窗户对面三楼是一家工厂的食堂,每到开饭时间,几个穿着工装的女孩总会透过窗户一脸好奇地踮起脚尖,朝我这边张望着,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我。她们在三楼,我在二楼。透过窗户这扇门,我看见这些女孩细嚼慢咽的样子,心生羡慕。我每天精打细算,把一天的花费压缩到最低。
我以床铺为凳子,手提电脑放在一张简易的可折叠的桌子上。我弯曲着身子敲打着键盘。两个月下来,我出现了腰肌劳损的症状,一股酸痛聚集在腰间,酸痛不已。
出租屋的铁门形同虚设,一整天,我几乎不出门。深夜,实在憋不住了,我才会打开门,走至月光下,慢慢奔跑起来。在一个废弃的烂尾楼里,我冲着寂静而又苍茫的夜空大声嘶喊咆哮着,以此来宣泄自己内心的压抑和孤独。
半年后,在莲姐的推荐下,我进入当地一家政府单位编一本文学内刊,生活终于安定下来。我租住在离单位一公里路的博夏社区。一室一卫,卫生间外面是一个狭小的厨房。我从二手旧货市场淘来一个床头柜,床头柜恰好可以摆放跟随我多年的笔记本电脑。在政府机关单位,我小心翼翼地工作着,寡言少语,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栋六层楼高的公寓,每层有五个房间。一楼入口处安装了坚硬的不锈钢防盗门,租户需要凭密码刷脸才能进来。二手房东是我的老乡。木制的房门漆成了灰黑色,右手敲门,单薄的木板发出咚咚的响声。住在我对面的那对年轻夫妻经常吵架,身材健壮的男人酒醉归来,屋内的灯亮着,敲门却不应。借着酒劲,他一脚飞踹过去,门砰的一声裂开了。紧随着女人的哭泣声透过门和墙传到我耳里,我隐约感到无形的东西摔落在地发出破碎的响声。
夜色如潮水般涌来。我疲惫地回到狭小的出租屋里,躺在床上,世界的喧嚣暂时隐遁而去,寂静把我淹没。两个小时后,寂静迅疾被再次袭来的喧嚣吞噬而尽。楼下是烧烤店,喝酒划拳的喧闹声如长了脚一般沿着墙壁攀爬而上,透过窗户进入房间,不时冲击着我的耳膜。对面房间三岁的小男孩正哭泣着,发出嘶哑尖锐的声音。整层楼呈一个凹形,我住在最里的一间,仿佛受到两面夹击,一步步被敌人逼到了绝境之中,无边的声嚣漫上来,把我淹没。
次日,我特意去手机店买了一副不错的耳机。深夜,我戴上耳机,听着伤感的音乐,世界的喧嚣顿时被我排除在外。
我渴望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门和窗。房子是一个人的栖息地,藏身之所。夜色如一团团黑云压了下来,倦鸟归巢,藏匿于枝繁叶茂遮蔽下的鸟巢里,世界顿时安静下来。
3
五年后,我用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积蓄买下一套宽敞的二手房。入住那天,躺在柔软的沙发上,看着窗明几净的房间,感受着房子里弥漫着的温馨与安静,一股别样的温暖在心底流淌开来。
安静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成无边的寂静与孤独,它们如潮水般袭来,把我淹没。我怀念出租屋的生活。周末,我常步行到曾经租住的博夏社区买菜。
彼时住在出租屋,房东是老乡,说着一口浓重的江西永新口音,听在耳里倍感亲切。每天下班归来总会跟他聊天唠嗑,仿佛回到了千里之外的故乡。出租屋的铁门外是一条街道,清晨或者薄暮时分,本地的商贩错落有致地占据满了街道的左右两旁。置身其间,仿佛回到了故乡的墟上,弥漫着浓郁的烟火气息。
城市的小区,出入都需要门禁。一次进入小区大门,我忘带门卡。保安见我面生,三番五次地询问,直至我报出房号,他才放行。小区的保安看着外卖员面露不屑,经常与外卖员发生争执。一个外卖员忍无可忍,转身疾步从一旁的小卖部掏出一把刀冲上去。刀的语言是无声的。锋利的刀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保安见状拔腿就跑。
门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紧闭的大门里藏着一颗颗设防的心。
“土,是农民扎根在泥土中的真实感,是对大地的归顺与感激,是一种生活的虔诚和踏实。乡村是熟人社会和人情关系盛行的无形秩序维持的。乡土社会重视安土重迁,秉持着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原则。”
在乡村,几十年如一日的相处下,乡民对彼此的生活习惯烂熟于心。侧耳细听远处传来的脚步声就能判断出来者是谁。我们的祖祖辈辈生于斯埋于斯,无法舍弃。
疏离慢慢从电梯里衍生出来。在电梯的作用下,人慢慢推离地面。在城市,人脱离大地,处于悬空状态。不断垒起的高楼大厦把人悬在高处,疾驰的汽车让人和地面隔着一块坚硬的铁皮。在乡村,人终日是紧贴大地行走的,浑身弥漫着泥土的气息。
在城市各色小区,邻居如同虚设,每家每户都房门紧闭,过起自己的日子,互不相关。一棵棵从乡村移植到城市的树,风尘仆仆的模样,彼此不明底细,分不清来路。
对面住着的邻居是一家三口,男的每天往返于广州上班,女的专职在家带孩子。
那日早上,我拉开门正欲去上班,见对方门口放着的一包垃圾渗出的污水已流到我家门口。彼时正是盛夏时节,污水散发着恶臭。忍着满腹的气愤,敲响对面邻居的房门。开门的是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人。我指了指从垃圾袋里渗出的污水。女人见状看了我一眼,把门口的垃圾袋提进门内,而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了。晚上下班归来,我见地上的那摊污迹还在,嘟噜了几句,进屋拿出扫把把地拖干净。
几日后,相同的情况又发生了,袋子里发馊的牛奶发出阵阵馊味,一只蟑螂透过门的缝隙迅速窜入我屋内。我一脚踩踏过去,却踩了个空,蟑螂早已躲进墙壁的缝隙里。忍无可忍的我急促地敲对方的门。“这是我自家的门口,又没放在你那里,你凶什么?”女人的这句话点燃了我心中的怒火。我和女人争吵起来,女人指着我的鼻子骂,说你一个男的欺负一个女的算什么。“到底是谁欺负谁?你还讲不讲道理?”我大喊道,声音回荡在楼道里。附近的邻居见状纷纷出来围观。
周末,手机忽然尖锐地响起来。“我是住在你对面的那户人家的老公,我在楼下,你下来一下,我跟你聊下前天发生的事。”我刚出楼梯,只见一个满脸胡须的男人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我顿时人仰马翻,摔倒在地,正欲起身,又被对方一脚踹翻在地。“谁叫你欺负我老婆的?谁给你的胆子?”男人叫嚣道。我正欲上前还手,不料被下楼的邻居给拉住了。
迅速报警,警察查看监控后把胡须男拘留起来。动手打人,男子面临着刑拘或者七八万的赔偿。嚣张的男子在派出所内立刻了下来,他说话变得结结巴巴,双手微微颤抖着,不停态度诚恳地向我道歉。男人说这段时间在公司很累很压抑。我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起身走开,不料他女人抱着不到三岁的孩子走到我面前赔不是。
在旁人的不断劝解下,我最终选择了和解,接受了对方的赔偿。
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做噩梦,满头虚汗地从梦中惊醒过来。梦里,有人拿着一把刀追杀我,我拼命地跑,直至跑到悬崖边。刀刺来的那一刻,我纵身一跃跳入悬崖。我通常在此刻惊醒过来,窗外夜凉如水。
半年后,对方卖掉房子搬离了小区。新住进来的房主是一对中年夫妻,面相和善,在附近的菜市场买菜,两个儿子正上初一。
一天,我下班归来不久,敲门声响起,杯弓蛇影的我如临大敌。打开门,却见是对面的邻居。男人手里拿着一把包菜和蒜薹,说,今天货进多了,还剩余很多,挺新鲜的,你拿着炒着吃。男人说话时,脸上那抹笑荡漾开来。我连连道谢,不好意思地接过来。关门,看着桌子上静静放着的新鲜包菜和蒜薹,我脑海里就浮现出年幼时五额婶经常给我家送菜的场景。
门还是那扇门,却因门内人的不同而发生巨变。
4
许多年过去,风叩门环发出的清脆响声不时在我耳畔响起,它不停敲击着我的胸膛。这是记忆中的乡村才会出现的温馨画面。一扇门和一对环背后是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家。夜色潮水般退去,晨曦缓缓洒落在屋舍的一砖一瓦上。门上的门环威严地扣于门面之上,它是最先宣告客人到来的使者。
多年过去,热闹的村庄深陷在无边的孤寂里。
屋前屋后的邻居大门紧锁,只剩五额婶和我母亲固守在家。一扇扇灰旧的大门紧闭,门梁上,一只蜘蛛倒悬在蜘蛛网上,静静地等待着猎物的靠近。偶尔的一个行人走近,急促的脚步声响起,蜘蛛闻声迅疾躲藏到暗影里。
紧闭的大门里危机四伏。2013年深冬时节,屋外阴雨连绵,寒意逼人。独居在村尾的八字婶一连三日房门紧闭。敏感的五额婶每天从八字婶家门口路过,顿觉蹊跷。她找了附近的几个村里人前去敲门。屋内毫无回应。拨打手机,片刻后却传来手机熟悉的铃声。众人顿觉不妙,疾速撬开门,见八字婶僵硬地躺在地上,双目圆睁着,浑身早已冰凉。原来,三天前略感风寒的八字婶在镇上的卫生所打完点滴已是深夜,回到家中不到一个小时,胸口的阵阵剧痛突袭而至。她捂着胸,瘫倒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八字婶的死如一块巨石砸入寂静的村庄,掀起阵阵波澜。八字婶的死敲响了警钟。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异乡,人们纷纷隔三岔五打电话回家。五额婶她大儿子昌华特意打电话给我母亲,希望我母亲没事多去他家里转转,跟五额婶唠唠嗑。
寂静的村庄,母亲和五额婶相互搀扶着穿越一个又一个漆黑的夜晚。
2016年仲夏时节,夜半醒来的母亲隐约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趴在窗前,朝屋内张望。母亲浑身禁不住直冒冷汗。几秒钟后,镇定下来的母亲忽然重重地咳嗽一声,而后忽然起身下床,疾步朝窗户边走去。窗外响起慌乱的脚步声。脸紧贴着窗户,母亲看见一个瘦削的身影迅速消失在暗夜里。惊魂未定的母亲不敢出门,推开窗,大喊着五额婶来给自己壮胆。五额婶闻声从睡梦中醒来,摁亮院落的灯,走出院门,安抚着母亲。此后几天,五额婶院里的灯一直亮着。忽几日,母亲从墟上买来一只成年的黄狗。一个月下来,在母亲的细心饲养下,老黄狗成为家里忠诚的一员。暗夜里,蜷缩在门洞里的大黄狗听到风吹草动的声音便即刻站立起来,作出咆哮状,狂吠起来。大黄狗的存在是一种有力的威慑。
春节将至,擅长书法的妻子特意买来红纸,写好春联,让我早点贴在门口。寂静的午后,我小心翼翼地把春联张贴在门的左右两端。两岁的女儿站在一旁,一脸好奇地看着我。一梯三户,城市小区的过道狭窄,仅容转身。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年幼的我站在老屋的门口,双手扶着梯子,抬头看父亲张贴春联。同样的场景,只是故乡变成了异乡。
春节将近,在异乡讨生活的人们回到了熟悉而陌生的村里,在年复一年的返乡里,他们苍老下来。
寂静的村庄顿时变得热闹起来。一扇扇紧闭了一年的大门敞开着,落满灰尘的家具在清水的冲洗下重新焕发光亮,结满蜘蛛网的窗户恢复至它固有的模样。
城市的气息侵袭到乡村的每个角落。父亲当年制作的一扇扇结实的木门,变成了坚固的不锈钢防盗门。一栋栋三层高的新房拔地而起,矗立在大地上。祖母的百年老屋夹杂在中间,仿佛一个破旧的补丁。
作为木匠,父亲是门的制造者。村里那一扇扇崭新的木门都是他用心制作出来的精品。旧时,父亲沿着那条小路穿过大半个村子,看着一扇扇熟悉的大门,父亲眼底满是骄傲。
如今,走至老屋的地基上,曾经耳鬓厮磨的老屋变成了一摊破碎的瓦砾,乌黑的门板此刻横躺在地,沾满灰尘和水渍,雪花把它淹没。我找来扫帚清除门板上积落的雪花,年幼时在门板上留下的一条条刀的划痕依旧清晰可见。我是笨拙的刻舟求剑者,门上的印痕还在,生命的小舟在时光的河流里已渐行渐远。
村里那一扇扇敞开的大门无形中仿佛又关上了。村里人聚集在一起不再谈论庄稼和稻谷,不再谈论播种和稻田。他们谈论的是谁家的儿子一年挣了多少钱,谁家的媳妇又生了一个儿子,谁家又在外面买了一套房子。
竹婶家也仅距我家几十米远,但母亲和五额婶却与她来往较少。
竹婶的儿子在深圳开厂,五年前推倒老家的旧房,盖起了一栋四层的新房,光装修就花了七八十万。房子装修好后,竹婶吩咐儿子在房子的四周安装了监控。住在隔壁的五额婶见了挂在墙壁半腰的监控,很是愤慨。监控的范围辐射到她家的院子和厨房。
“有钱了不起吗?防贼防到我这里来了。”五额婶气呼呼地说道。一墙之隔的竹婶正在洗菜,听了五额婶的话,气得叉腰骂了起来。两人对骂了很久,五额婶越想越气,跑到屋里,抄起竹竿,把墙上的监控一下子戳了下来。竹婶见了,两人顿时扭打在一起,一旁买菜归来的路人见了急忙过来劝架,把两人拉开。
做了几十年和睦邻里的竹婶和五额婶就这样结下了梁子,彼此互不往来。
竹婶这栋新房给她攒足了面子,她一下子扬眉吐气,腰杆子也挺了起来,跟村里人说话时也变得阴阳怪气。
为了防盗,竹婶的儿子买了一条足有腰身高的大狼狗,让竹婶养着。夜幕降临,微草绿柳在夜风中左右摇曳,屋外一有风吹草动,狼狗就狂吠不止,两只前腿不停挠着铁门,一副欲破门而出咬人的模样。白天,狼狗见有陌生人从铁门口走过,喉咙里发出呼呼声。固守在村子里的老人担心孙子孙女的安全,都纷纷叮嘱他们不要从竹婶家门口过,宁愿绕道走也好。
监控是卫兵,是日夜不知辛劳看守大门的守卫。监控是情感延伸出来的东西。竹婶有心安装的监控无形中伤害了邻里的情感。
监控事件后,竹婶和五额婶没再说话。她们是近在咫尺的邻居,却形同路人。
5
2021年深冬时节,五额婶的腰疼越来越严重,她忍着。她不想躺在床上养病,不想闲着,一闲下来她就感到浑身发痒。看着满菜园子的翠绿,看着满地在寒风里迎风招展的油菜苗,她心理就觉得舒坦。
三年前,五额婶被诊断为腰椎骨腐蚀严重,有一个地方因为腐蚀严重有一个手指粗的缺孔。医生嘱咐她千万不要再干重活,不要忙于农事。但忙了一辈子的五额婶闲不住,病痛稍有缓解,她就下地干活,种稻谷种油菜,年近八旬的她弓着身子穿行在那亩她耕种了一辈子的稻田里。
五额婶还是累趴下了,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嘴唇苍白,眼窝深陷,脖子上的青筋暴露。她已半个月滴米未进,靠打点滴续命。
五额婶奄奄一息的消息传到隔壁竹婶的耳中,她心底咯噔一下,颤颤巍巍地往五额婶家走去。她们以前是好姐妹,自从上次因监控一事闹掰了后,就再也没往来,一晃已是八年。
竹婶走进屋,叫了声五额婶,抚摸着五额婶的脸,粗糙的手微微颤抖起来。
“你来了呀。”五额婶微张嘴巴,轻声说道,声音细如游丝。
“我对不住你呀,妹子。”竹婶说着说着,眼角溢出一滴浑浊的泪来。
三日后,雨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五额婶在这个下雨的清晨离开了人世。
县火葬场在郊外,四周山林寂静,偶尔有一只鸟发出阵阵悲鸣声,划破寂静的天空。五额婶她儿媳和两个女儿趴在她身上抽泣着,火化的时间已到。见完最后一面,五额婶被推进了火化炉。随着火化炉的那扇门被轻轻关上,生命的大门也随之关闭,死亡的大门敞开着。
“路上小心点,我们总会见面的。”我想起电影《入殓师》里的那句台词。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死是生命的一部分,亦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再相见时,五额婶变成了三公斤重的骨灰,亦如八十年前,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声,她来到尘世的重量。
每个人都要跨越死亡这扇门。次日,母亲颤颤巍巍地走在送葬队伍里,坚持着把五额婶送上山。从山上下来的母亲独自在房间里流泪。
五额婶走后,她的儿子儿媳返回了广东的工厂上班,屋子彻底空了下来,房门紧闭,那盏曾经为母亲亮着的灯未曾再亮起,几个月后结满了蜘蛛网。五额婶远在山上,却也在母亲的心底。
屋外狂风大作,大雨即将来袭。风把大门和窗户吹得哗啦响。残存的门环在暗夜里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仿佛异乡归来的游子正轻叩门环。
母亲颤颤巍巍地下床,把一扇扇窗户关好。屋外夜色苍茫。站在窗前,望着五额婶居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母亲脑海里浮现出那盏院落里一直亮着的灯。此刻,那栋房子房门紧闭,淹没在无边的夜色里。
母亲变得更加孤单起来,老黄狗暗夜里发出的阵阵狂吠声映衬着她的寂寞与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