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路|金龙贺岁·中国作家2024迎春专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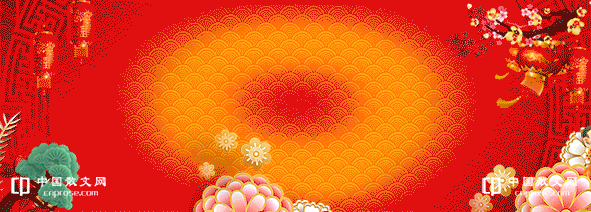
朱大路|金龙贺岁
中国作家2024迎春专刊
作家简历
★
朱大路 上海人,1947年出生,1965年进《文汇报》社,2007年退休。其中,在“笔会”副刊编杂文20年。高级编辑,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全国各地杂文学会联席会组委会副会长,上海浦东新区杂文学会会长。著有散文杂文集《乡音的色彩》等两本,报告文学集《盲流梦》,传记集《上海笑星传奇》,长篇小说《上海爷叔》等四本,主编《杂文300篇》等三本。先后参加全国各种散文、杂文大赛,七次获得一等奖,四次获得金奖。
“古董”
这已是多年前的事了。
我因写《上海笑星传奇》一书,获知黄金荣的总管家程锡文,外号“夜壶阿四”的,当年曾与多位笑星有往来,如今还活着,八十岁了,便去找他。
临街的小店,晚饭后,早就熄灯关门,阒其无声了。我等在店门口。对面马路,踽踽过来一老人,弓腰驼背,拄着手杖。他颤着手,打开门锁,领我进店堂。店内摆一小板床,老人晚上就借住此地,而一早七点半便离开。
我面前的老人,在当年的上海滩上也曾风云一时。黄金荣的意图,要经过他朝下贯彻;三教九流的需求得疏通他,由他往上递呈。而此刻的他,目光迟滞,动作缓慢。此一时彼一时,恍若隔世也。
我说,我是把他当老师,来了解旧上海轶事的。我递上刚买的一袋苹果。他很高兴,也有点惊讶,因为他孤独,很少有人到这里同他谈谈话。今天,我居然走进这个被遗忘的角落。
他记性好,不善说理,却长于形象思维。除了谈旧上海的笑星,便是回忆黄金荣,但不是摆年谱、叙大事,而是一枝一叶,一鳞半爪,进行白描。说黄金荣平日喜戴六角帽,平顶,上有珊瑚结子;寒冬腊月,则戴一顶围上纱的藤壳帽,脚穿兔子棉鞋;出门坐雪铁龙汽车,油用得伤;每天抽鸦片,都是巡捕房里充公来的。所住“黄公馆”,是在乡下人房子旧址上翻造的,五上五下。还说,“大世界”执照别人开不出,唯有黄金荣能解决。艺人演戏,没有黄金荣送的匾,流氓会来闹。讲得起劲了,露出得意之色,说黄金荣曾关照儿子:“外面来客人,你不要管,由程锡文来管!”
我面前,仿佛是一件出土的古董,有锈斑,有裂纹,却能折射历史的光。
过些日子,我约老人到我家谈。他蹒跚着来了。不肯吃饭,只肯“聊聊老上海”。他谈“德本善堂”,谈“半淞园”,谈虹庙的道士,谈“蜡烛小开”,谈“斧头党”和马永贞,谈三十年代的“白锡包”和“三九牌”香烟。停了停,又用俏皮话描述商人黄楚九的尴尬、邋遢,说黄楚九开“日夜银行”,是为了适应赌市需要。外国水手上码头晚,把衣服送进小押店抵押,小押店向“日夜银行”借钱,等水手赢了钱,再赎衣服,还钱。有段时间黄楚九资金周转不灵,想求救于虞洽卿,虞恰巧在外地,帮不了忙,“日夜银行”只得倒闭。
我仍不满足。春天,当树枝爆开嫩绿的芽,我再次踏进临街的小店。这次我买了一袋蛋糕去。我想了解城隍庙文化,它是海派文化的一枝。程锡文当年是城隍庙“出会”的总指挥。出会,每年三次:清明、七月半、十月初一。于是,在这个春风微拂的晚上,我听着老人的叙述,眼前突然浮现出一支近万人的出会队伍。早晨九点“起升”,有的肩扛城隍“老爷”,有的拖扁担,有的吊香炉,从城隍庙一路走来,经过南市银辉桥,歇一歇,晚上八点“回衙”。回去时,红灯笼里点蜡烛,红闪闪,一条火龙,煞是好看。老人对我解释:什么叫“飞”,什么叫“抢轿”,什么叫“恭出”,什么叫“班首”,什么叫“马执士”。
我们都喜欢侈谈海派、京派,但这真正的海派货,我们又研究了多少呢?
以后,我因忙,好长时间没去。一回,我路过小店,发现小板床不见了。老人搬走了吗?住院了吗?终于,我从邻家得到消息:他死了,走得很孤单。
我踯躅在小店门前。秋风卷枯叶,贴着路面,一掀一落,飘向远处。我想,这世上,又少了一件“古董”。当它是一种“寂寞的存在”时,人们感觉不到什么,而如今,难免使人怅然若失了。
深山里的周瑜子孙
汽车开到山间小路口,进不去了。下车吧,徒步上山!
深山叠翠,岚气缭绕,涧水淙淙,飞鸟啾啾。三十万亩原始森林,让这里的每立方厘米空气,含有负氧离子30万个单位。在大城市受雾霾困扰的诸公,何不到此,轻松洗肺?
眼前,是江西资溪县马头山镇昌坪村的周家村小组。整个村,已成“空壳村”,十几栋废弃了的旧屋,孤寂,冷清。周家祠堂前,茅草齐腰,墙上布满绿色的“爬山虎”。是“城镇化”脚步,催动周家村村民整体搬迁,进城镇安家。资溪是“中国面包之乡”,资溪人在全国各地开了几千家面包店,不少经营者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如今,走出去的“面包大军”中,又闪动着周家村人的身影。
但有人,却不想进城发财,甘愿独自一人留守深山——这就是今年61岁的周国荣。朝朝暮暮,守在这里,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二是要胆大,毒蛇爬过来,不怕;野猪蹿出来,不怕。笃悠悠,一位淡定哥!
他不计报酬,守护国家原始森林,严防火灾发生,让山上的猕猴们“安居乐业”。这里进山门,须登记车号,看身份证。有外人进来,他必定打电话上报。发现异样情况,马上报警。前不久,有二十多对情侣,想来山上烧烤,给恋爱“添火加温”。他不禁止恋爱,却禁止明火烧烤,这是“防火细则”规定的呀。情侣们只好取消此一计划。
他尽心尽责,守护村民财产。这里的屋子都不锁门,断壁残垣,零散家什,本不值钱,他看重的是对祖祖辈辈感情的守护与升华。墙上残留着电表,门上残留着“功业永存”的横批,蓄水池的管子里,还滴着山泉水。高脚楼虽然拆了,老奶奶当年出嫁必走的河边老路,依旧横贯着。老林邃谷,遗存着“瓯越文化”的碎屑。这是带暖色的教材,供外迁的村民清明节回来祭祖时,温馨地复习。
周国荣的儿子——原周家村小组的主任,听说我们去,特地从别处赶来。他赞扬留守的父亲,还追述家谱:“我们周家是龙图世家,老祖宗里,有宋朝的周执羔,中过榜眼,做过龙图阁大学士。”
没曾想,布衣野老,接续着显贵门祚。
“再数上去,到‘三国’,老祖宗就是周瑜!我们属于周瑜第二个儿子传下来的那一支。”周主任说。
呵,他们是周瑜的子孙!我有点激动了,想从周国荣父子脸上,寻觅“三国”周都督脸型的基因组成。
“周瑜是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他们父子俩,都为老祖宗自豪,同时想凭自己的作为,证明周家这一支是争气的。
起风了,满山绿叶,飒飒作响。感人的是,山径边一株近千年的红豆杉,用树枝托住长歪了的樟树,不让它倒下,有点“相依为命”的意思。
望着黝黑、清瘦的周国荣,我在想:周瑜的子孙,对清贫简陋,甘之如饴,只为完成两个字:守护!正如北宋思想家、资溪人李觏的诗所说——“富贵浮云毕竟空,大都仁义最无穷。一千八百周时国,谁及颜回陋巷中?”
周家老屋前,我们吃了“原生态”午餐:野猪肉、小溪鱼肉、竹林鸡蛋、山泉水调拌的野生蜂蜜,等等。我道了声“谢谢”。
“不能说‘谢’!”周主任说,“我们资溪人,讲话有忌讳,比如‘帽’的土音是‘没有’,‘帽子’就改称‘有子’。‘谢’是‘凋谢’,一般不讲。”我连忙改口:“那就说:好,棒,下次再来!”
是的,周瑜子孙,绵延至今,不希望“凋谢”。
作家存在的理由
有使命感的作家,是心心相印的。
1962年,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约翰·斯坦贝克,上台发表受奖演说时,动情地引用了威廉·福克纳的话。
言辞是这样组合的——
“人类一直在通过一个灰暗、荒凉的混乱时代。我的伟大的先驱威廉·福克纳在这里讲话时,称它为普遍恐惧的悲剧:它如此持久,以致不再存在精神的问题,唯独自我搏斗的人心才似乎值得一写。
福克纳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人的力量和人的弱点。他知道,认识和解决这种恐惧是作家存在的主要理由。”
福克纳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隔十三年,他的逻辑,思路,用语,被斯坦贝克重申了。
当然,斯坦贝克也作了发挥——“作家有责任揭露我们许多沉痛的错误和失败,把我们阴暗凶险的梦打捞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利于改善。”
打捞梦,暴露梦,改善梦。
“人本身成了我们最大的危险和唯一的希望。”
危险与希望,都交织于人本身。
这就是斯坦贝克!
1929年10月29日,这个“黑色星期二”,股票市场突然崩溃,让美国一步步,滑入经济大萧条中。
人,是如此脆弱,恐惧。命运,是如此危如累卵,不堪一击。一边,是资本家、农场主,将白皎皎的牛奶倒进河里,将黄灿灿的玉米当燃料烧;一边,是日益贫困的民众,大量失业,四处流浪,食不果腹,疾病缠身。生活像一出闭不了幕的恐怖剧,让人心惊肉跳。与命运搏斗的人,无处不在,却看不到希望所在。
面对如此现实,斯坦贝克把同情心“始终赋予被压迫者,赋予不合时宜者和不幸者”。作家的使命感,迫使他不像一只小耗子那样叽叽吱吱,而是像一头狮子那样发出吼声!
他的目力洞幽烛微。他的文笔缜密精致。这绝对是属于斯坦贝克的生活积累,情感架构,叙述节奏,形象酝酿。小说《人鼠之间》诞生了。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着,渐渐进入读者的视野。前面那个矮的,是乔治,眼神犀利;后面那个高的,是莱尼,眼睛大而无神。装束倒是差不多——都穿工装外套和工装裤,都戴陈旧的黑帽,都扛着毛毯卷儿。乔治原先认识莱尼的姨妈,莱尼从小跟着他姨妈,是姨妈将他养大。姨妈死了,莱尼就跟着乔治外出打工。不料莱尼在先前的农场闯祸了,乔治只得带着他奔赴新的农场。乔治觉得莱尼像个小孩子,本质好,没有任何坏心眼,但天生低能,说话、做事傻乎乎,需要乔治点拨、关照,否则总是出纰漏,吃大亏。莱尼想离开乔治,一个人去山里,乔治出于友谊,不同意,认为这样做,莱尼会被人当作野狼一枪打死。
大萧条时代的人,灰心短气,有严重的生存危机感。想摆脱恐惧,最符合逻辑的思维,便是找到一块能够安身立命的绿洲,涸鱼得水,夹缝求生。乔治带着莱尼,来到一个农场打工。他俩憧憬着——卖力干活,勤勉挣钱,然后买一块地,上面有自己的房子、卧室、厨房、鸡舍、耕地和果园,无需累死累活地干,每天只要工作六、七个小时就够了,收割自己的庄稼,想吃什么,就种什么。“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谁也不能解雇我们。”在农场断了一只手的看门人坎迪,平日只能做清扫工作,却以自己微薄的收入,加入乔治和莱尼的队伍,遐想着这愿景成真以后的幸福生活。乔治虔诚地说:“上帝啊!我打赌,我们能成。”倒是黑人马夫卡鲁克斯头脑冷静一点,他不无调侃地告诉莱尼——
“我见过成千上百的人,他们背着铺盖卷儿,顺着公路来到这里的各个农场,他们的脑子里也是装着跟你们一样的这个愚蠢的念头。他们来了,走了,完了又来了,每个人都他妈的想着将来要有一块地。可他们中没有一个有了一块地的。就像天堂难以企及一样。”
但莱尼喜欢柔软的东西——比如兔子——他企盼着赚钱养兔子。他的口袋里还装着死老鼠——走路时,喜欢用大拇指摩挲它,以致乔治严厉地命令他把老鼠掏出来,并一把拿过来,扔到了对岸的树丛里。而莱尼又趁乔治要他去捡干柳枝来把豆子烧熟当晚饭之际,隐入树丛里,将那只开始腐烂的死老鼠偷偷捡回来,再次被乔治抛向远处正在暗下来的树丛里!
概念与僵化的思路,永远与优秀文学无关。斯坦贝克在大萧条时期深入调查过萨利纳斯和倍克斯菲尔德地区流浪雇工的生活现状,还刊登过新闻报道,对流浪季节工人的形象耳熟能详。因此,低能儿莱尼的命运,就被作家匠心独运,安排得既在情理之中,又绝对出人意外。
正是莱尼力大无穷、却又酷爱柔软的东西,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农场主的儿子柯利,拳艺不凡,曾进入黄金拳王赛的决赛,但在对莱尼无理取闹时,被莱尼捏碎一只手。为了不被人笑话,只得说是手被机器碾压了。柯利的妻子平日不喜欢柯利,觉得他不好。她有自己的理想,想当演员,穿漂亮衣服,出风头。她不理解莱尼这个傻子为什么喜欢抚摸兔子和老鼠这些柔软的东西。她告诉莱尼,她的头发是柔软光滑的,要莱尼来摩挲,结果莱尼越摸越起劲。柯利的妻子担心头发被弄乱,叫他松手,莱尼捂住她的嘴和鼻子,不让她喊出声。莱尼力大无比,只摇晃了几下,柯利的妻子就没有声息了——她的脖子被莱尼拧断——死了。
合伙去买地皮、构筑幸福家园的美梦,就此破灭!莱尼知道自己闯了祸,逃到山脚下的灌木丛中。他依然离不开柔软的东西——眼前出现幻觉:一只特别大的兔子,在嘲讽他是“傻瓜蛋子”,“连给兔子舔脚的资格都不够”,说如果让他来照顾兔子,兔子会挨饿。这时,乔治赶到了,由于听到了树林里响起的杂沓的脚步声,他担心莱尼会被柯利抓住,动用私刑,残酷折磨至死,便出于对莱尼的疼爱和保护,一枪把莱尼打死了。然后,就坐在河岸上,“楞楞地看着他刚才扔掉枪的右手”。
《人鼠之间》,这题目,比斯坦贝克原先给小说定的题目《偶发事件》,好多了,既形象,又有寓意,耐得住咀嚼。鼠是灵动的,也是脆弱的,当鼠窝被捣,失去栖息之所,鼠类只能逃窜,任凭雨雪风霜,恶人践踏,充满了恐惧,最后往往不得善终。乔治、莱尼一类的流浪农业工人,命运也如老鼠一般,凄苦穷困,流离失所,在恐慌中,了此一生。
可贵的,还在于这小说对人性的设计,饱含戏剧因子,所以改成剧本上演,便受到追捧。戏剧,讲究人物、场面、悬念、冲突,引发观众好奇心,有可看性,这对当代热衷于快文化,沉湎于脱口秀、抖音,越来越没耐心品读小说的一代年轻读者,有感召力。
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恐慌景象,给斯坦贝克带来灵魂的冲击,他决意坚守作家的使命,用手中的笔,点染恐惧时代的图景,犹如狮子一般,发出吼声。他的《愤怒的葡萄》,承继了《人鼠之间》直面恐惧的创作传统,写农民负债、破产、为实现美梦而长途迁徙,内容更具斗争锋芒。
从福克纳到斯坦贝克,真正的文学,是延续的,固执的,坚守的。
我们需要汲取的,恰恰是最能观照现实的。福克纳说:“人者,无非是其不幸之总和而已”。人类的困境,绵延不断,会重复,也会加剧。当前,就世界范围而言,几十年的和平红利,已消费得差不多了,战争的烽烟,此起彼伏。不少地方的经济,出现垮塌征象,企业倒闭,生意亏本,求职无门,股市暴跌。新冠疫情把世界搞得疲累,核污水肆无忌惮向公海渗透。地球的气候变化莫测,或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或洪水横流、似吞似噬。人的命运升腾跌宕,起伏不定,为填饱肚子,为还清债务,为安身立命,为求得发展,寻梦者恐惧频现,梦破者悲剧不断。历史的行进轨迹,似乎是在按人的愿望铺展,似乎又出现种种意外,让人在历史面前,显得渺小、低微。而认识和解决这些恐惧,正是作家存在的理由。
毕竟,文学不是供托钵僧消遣的游戏。
每年十月,公布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结果,都是一道风景。失之交臂者,腹内五味杂陈。吃不到葡萄者,嘀咕着葡萄是酸的。设立“赔率榜”的博彩公司诸公,在算计榜单的盈利几率。但可以相信,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巨匠——深知作家存在的理由——他们会以笔端的创作是否不辱文学使命,来冷静地评估自己,而不会只盯着“赔率榜”发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