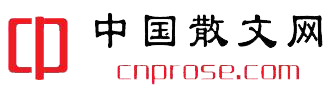任白:诗歌用飞行呈现生命与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任白,吉林省吉林市人,诗人、作家。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出版诗集《耳语》《任白诗选》《情诗与备忘录》《灵魂的债务》和中短篇小说集《失语》。现居吉林省长春市。
一、你是从哪一年开始诗歌写作的?最早激发你写诗的灵感是什么?
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诗歌写作的。1979年,我进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汉语言文学,当时中文系和校内其他院系有各种各样的文学社团,文学氛围浓厚,加入文学社团敦促我开始阅读和写作,也算是校园生活和青春期的一种伴生物。
二、请选择2——3位对你的诗歌创作最有影响的古今中外诗人和艺术家。
这种选择并不容易,几十年来,每个具体时段都有些或大或小的变化。目前从我个人的诗歌观念讲,切斯瓦夫·米沃什是对我启发影响最大的前辈诗人。在《诗的见证》这本小书里,米沃什从时代社会的现实语境和人类精神传统等多个维度,为诗歌确认了长久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也是任何时代诗歌创作的前提和基础,具体真切地阐释了“诗人何为”的重要命题。这非常重要,国内有些诗歌写作者可能很少从这样的角度想问题,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创作生命非常短暂,作品也缺少应有的深度与广度,无法深刻地言说我们的生命与生活。米沃什郑重地批评了20世纪诗歌的“贫乏与狭窄”,它们要么在各种似是而非的观念里空转,要么在修辞的螺鰤壳里做道场,沾沾自喜,言不及义,是一种“孱弱的小诗歌”。第二位聂鲁达,这是与我个人气质完全不同的诗人,但他的缤纷意象和令人瞠目的想象力永远令我叹服,也是丰富我个人创作的一个重要参照物。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说,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梦想”。聂鲁达恢复了语言的混沌与神奇,使之与大自然保持同频,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赞辞!第三位我选北岛,他早期的诗歌创作和后来的散文随笔都是中国当代文学中难得的精品。凭借“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诗句,北岛进入了中国诗歌的万神殿,丰富了民族语言的表达,达到了新诗创作的极限高度,成为极少数能和中国古典诗歌前辈比肩的新诗代表性诗人。
三、请提供你自写作以来的10首代表作题目,并注明写作年代。
《于是我开始给你写信》(2016);
《那些时光》(2017);
《光年》(2019);
《失败的人》(2019);
《有一天》(2020);
《7月21日》(2020);
《人在找他活着的那一天》(2021);
《新年快乐》(2022);
《诗歌是古怪的物理学》(2023);
《山行记》(2023)。
四、你写诗一挥而就,还是反复修改,还是有其他写作方式?
短诗初稿往往一次性完成,但一般都会放置一段时间,回头再改,多次修改的情况不多。长诗写作时断时续,有时甚至会做方向上的调整,几十行上百行说废掉就废掉了,写完也会经历更多的修改过程。
五、你如何看待生活、职业与你诗歌写作的关系?
生活是思考的起点,是诗歌起飞的跳板。特别是在流派和观念的泡沫消散之后,生活水落石出,成为诗歌存在的基石。没有生活,诗歌往往会失去对象性和重量,处于不及物的悬浮状态,也由此失去与读者共情的基础,无法进入公共阅读,无法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但诗歌不能满足于对生活的简单观照,不能匍匐在生活表面,不能以爬行或步行的方式展示大地的平展、凹陷或隆起,它必须生出翅膀,用飞行呈现生命与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职业是一个机会,可以帮助诗人与世界建立一种深刻的连接。欧美历史上有些了不起的诗人都曾经担任过外交官,这种职业显然会给他们的诗歌世界带来一种不同的样貌,对不同文化的深刻认知,兼容的气度,更真切的丰富性等等。但我不认为职业是决定性的经验,优秀诗人总会以自己的方式超越个人经验,去实现自己的丰富与独特。
六、你关注诗歌评论文章吗?你写诗歌点评、评论和研究文章吗?
关注,但真正有洞见,对诗歌现状观察深刻、阐释清晰的文章不多。自己也写得少。
七、你如何评价现在的中国诗坛?
当下的中国诗坛呈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丰富性。最令人欣喜的是所谓“底层诗人”的大量涌现,从打工诗歌开始,近十年来自各行各业的底层写作者,用他们极富现实感,有着真切生活肌理的作品引起社会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余秀华、王计兵、陈年喜、李松山等作为他们中的代表性诗人,不但为我们贡献了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而且罕见出圈,为媒体提供了很多社会性话题。对这种现象,诗歌界有很多不同的评论,我的意见是,底层诗人的出现,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诗歌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巨大困境的人,无意中选择了诗歌作为自己抵抗绝望的工具,一方面安慰和激励了自己,另一方面使这些原本社会中的匿名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确认了自己的存在,这既是他们之幸,也是诗歌之幸。很难想象,他们在拿起笔写作诗歌之初,就有成名圈粉的奢望,只有自救自证的渴望驱使他们,说出自己的痛苦和挣扎,而这正是诗歌的真意。所以,很难说是诗歌救了他们,还是他们为诗歌重新确认了不竭的生命力。我个人觉得,无论诗歌界还是学术圈对这类诗人诗作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还有一个看起来同样十分意外的好消息,就是大量九零后甚至零零后诗歌写作者的出现。十几年前,舆论不乏诗歌将死的预判,无论阅读还是写作,年轻人都在远离诗歌,作为一个趋势,其必然的结果当然是诗歌的终结。然而近些年的实际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反转,大批年轻人开始阅读和写作诗歌,无论传统文学期刊还是像小红书这样的社交媒体上,都出现了他们的作品。和底层写作者一样,年轻诗人的出现同样说明诗歌的生命力,并不会因为传播工具的变化而消失。特别是在某些历史转折期,人的命运发生巨大改变的历史时刻,诗歌是陪伴人精神与灵魂的忠实伙伴。
此外,一些资深的经典性诗人仍在不断奉献力作,如胡弦、陈先发等,他们以深刻的洞察重建历史叙事,并试图用诗意的言说校正混沌现实。在经历了自己此前的创作高峰之后,仍然能找到新的支点,获得新的动力,非常难能可贵。
但老实说,今天的新诗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肉眼可见。虽然诗歌活动异彩纷呈,诗歌奖项鳞次栉比,但与创作数量和获取的社会资源相比,总体上诗歌创作实绩差强人意。优秀作品不多,值得关注并且引发热烈讨论的作品更少。所以,有青年学者认为中国新诗正面临空前困境,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困境论”也值得诗人和批评家们认真对待。
八、请写出你认为最重要的三个诗歌写作要素。
米沃什的同胞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有篇文章,叫《捍卫热情》,重点讨论了在现代诗歌身陷怀疑论的泥沼后,如何保持或重新唤醒热情。我非常认同,“热情”是我心目中今天从事诗歌创作的第一要素。当然这个“热情”既指生活热情,更指诗学热情。我之所谓诗学热情是指面对存在的虚无和荒诞,人所展示的勇气与优雅。它类似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也像肖斯塔科维奇在“每天准备被枪毙”的恐惧中不断写出澎湃的乐曲。这种热情是终极的,也是原初的,是所有热情的基础。只有这种热情才能驱动诗人们面对存在的重重围困,坚持思考与言说,坚持为人类据守和拓展精神空间,从而照亮现实,使所有物理空间成为人的家园、故乡和祖国。
其次,怀疑是热情的怨偶与诤友。没有怀疑的陪伴,热情可能流于轻率,甚至滥情。真正的热情必须经由怀疑的锻造,所以,今天的诗学一定是二元论的,它不能在一个支点上下注,不能在单一向度上倾其所有。一个多元世界上的单极诗学是可笑的、荒谬的,甚至是危险的。
第三个要素是想象力。如果说热情与怀疑是诗歌带有形而上意味的基础,那么想象力就是诗歌有形的翅膀。没有想象力,诗歌就会萎顿,就会丧失诗歌作为独特文体的资质。很久以来,新诗流行书写日常经验,但是没有想象力参与重构的日常经验和诗歌没有关系,它可能会是散文,或者小说,唯独不可能是诗歌。这也是今天诗歌写作的一个陷阱,诗歌必须长出想象力的翅膀,才能从日常经验的头顶起飞,离地一米也好,飞抵巡航高度也好,超越同温层也好,成为真正的诗歌,带领我们进入新的存在高度。